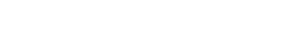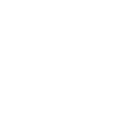我的家在南方的一个小县城,在当地算是个大家庭,有多大?这么说吧,以前每逢过年,全家都要例行照一张全家福,由于人多,在家里你呼我我喊你热热闹闹的了半天才出的了门,到全县最大的照像馆门前,一定有几个工作人员马上跑出来,迎接我们,每年来,都熟。经理反复嘱咐,走轻点走轻点,因为这虽然是全县最大的照像馆,又是两层楼,但一层与二层之间却是木板横梁相隔,且年月远久,常常有灰土往下掉,人一多上去总是显得摇摇欲坠,大有随时同归于尽的气势,总之我们家的人一来照全家福,大多数的人都会往外跑。。。呵呵。
说是大家庭,其实也只有九个兄弟姐妹,比那个《家有七凤》电视剧里的家还多二个,但我们的家庭结构却要复杂得多,九个人中五个是属于妈妈的,三个属于爸爸,而我是属于爸爸妈妈共同的,因为我的父母是再婚,我本不是计划之中,但那时工具不好用,又没有什么娱乐,所以我才有幸于不经意之中来到这个世上。自小我就觉得是在人的背上和自行车的后架上长大的,我出世的时候文化大革命已经开始了,平时都是哥、姐背着我,武斗时是爸爸用自行车载着我逃往二十多公里的外婆家,由于兄弟姐妺多,爸爸总是二个载一程,放下走,然后回头再载两个,以加快前进的速度,我们一家人总可以走走歇歇,但爸爸却在不停的骑着那辆吱吱作响的自行车,不断来回的走,我们走了二十多公里,爸爸却走了四十多公里,现在想起来爸爸在夕阳中脸上没有汗,却浑身被汗水湿透的情景,我总是有种想哭的感觉。
妈妈是乡下农村的一个小学教师,爸爸是县城机关的干部,由于兄弟姐妹多,总是吃不饱,吃饱成了我们家最大的一件事,小时候,在哥哥姐姐的眼里,我是最幸福的孩子,记得每次分东西,我总是比他们多一点,一点有多少呢?打个比方说,这顿饭的菜是香肠,一根十五厘米象姆指粗的香肠,四个人分,我总是能比他们多分近一厘米,别小看一厘米,哥哥姐姐其实是馋得不得了,因为这一小段香肠是这一顿饭唯一的下饭菜。连青菜了没有,当然更不可能有什么汤,饭也常常是数得清米粒的稀饭。对待这一小段香肠我们可是格外的珍惜,都舍不得真吃,每次只是吮一下,饭吃完了(因为是定量,不能说吃饱,只能说吃完),这段香肠仍然是完整无缺,五哥哥说了这么一句:要是有一顿香肠吃个饱,真是天底下最大的幸福。
时候,我们都要做份内的工作,我七岁就要煮全家的饭,哥哥姐姐也要洗衣服,搞卫生,打小工,除我外星期天定额每人一篓柴草,没有完成的不能吃晚饭,有一次五哥不知是偷懒还是确实找不到柴草,傍晚回来的时候用树枝架在篓里,上面只是簿簿地铺了一层树叶,不幸被妈妈用脚一踩,全塌下去了,阴谋败露,结果当晚只能喝小半碗米汤,只有不停的喝水。
有一次我在路上捡了两毛钱,高兴得要命,那可是值两个鸭毛的钱,如果我知道是谁掉的,我会还给别人,但交给pol.ice他也找不到失主,我只好据为已有了,拿回家告诉哥哥姐姐,都高兴得要命,经过讨论,决定拿去买水果吃,我和哥哥到门前的国营果品公司,见到有架子上有好多水果,有苹果、梨、香蕉等,无论是颜色还是香味,都让我们喉咙产生的一丝丝清泉不断的往上涌,使我们看着对方,都不约而同地咽着,但我们都知道那架子上的水果我们是吃不起,或说从没舍得吃,于是我们硬生生地收回我们的贪婪的眼光,投向架子旁边的几个破筐,里面才是我们想要的,那里是一些没有烂完的水果,把烂的地方抠掉,洗一洗,分门别类一字摆着,那价格比架上的要便宜得多,尽管有些水果只烂剩了一条心,我们可不管,因为烂水果是论筐买的,而且买水果的那些人我们很熟两毛钱可以买一大筐了,商量了一下决定买苹果,因为除了好久没吃苹果外,还因为吃苹果不会象吃梨一样老要拉尿。我递我那个白发伯伯二毛钱,指指放烂水果的筐,他笑着走出来,指着一个装得滿滿的一筐,说这筐。行了吗?我和哥哥高兴得差点要跳起来,那一筐足有三十多斤,我们知道他是照顾我们,连连点头谢谢,告诉老伯伯,我们先把水果抬回去,再还筐,老伯伯说行,两兄弟抬着一大筐不断滴水的水果,兴奋地回到家,避开父母(我可不想父母问钱是那来的。那是招打),偷偷藏了起来,就等晚上人齐了就开餐。
晚上十点,等父母都睡了,我们偷偷起床,搬出那张大饭桌(我们家人多,饭桌当然也大),点起煤油灯,再提来一桶清水,先把那些烂水果洗干净,全堆在饭桌上,然后一人一把小刀,自削自吃,姐还轻轻的唱起了歌,在这个桌子上,没有父母是否相同之分,这是我到现在也感到我生在这样的家庭是幸福的原因,三十多斤的水果不到半个小时,基本只剩下了一堆果皮和削下来的垃圾,可还有人心有不甘用手东翻翻西翻翻,企图再找一些没吃干净的,却一无所获。
好的时光总是不长,清理完战场,我们睡下(我们都住在一个大房子),兴奋的声音此起彼伏,大家都很兴奋,没有一丝睡意,不久,响屁声代替了说话声,亲兄弟们就先后出去了(那时只有公厕),不用说大家也知道,去厕所,结果半夜时分,公厕内外全是我的兄弟姐妹白花花的屁股,场面颇为壮观,拉了一夜,大家都是眼塌脸白,三哥挣扎着抬起头,说了一句,拉也值。第二天喝了一肚子水后,竟也全部都不药而癒。
在我的印象中,最怕的东西就是塔糖--那种有很多种颜色的、造型也很漂亮的打虫药,刚开始吃的时候,觉得甜甜的,还不错,只是吃后有点恶心,吃多了就怕,宁愿让虫子吃也不想吃塔糖,却不得不常常吃。
究其原因,还是饥饿惹的祸,那时是见什么吃什么,可不管是不是卫生,与饥饿比起来,卫生简直就是微不足道。而最容易得到食物的地方就是刚收获过的番薯地,里面总有没收干净的番薯或大一些的根块,放学后总会跑到那里一边走一边用脚翻开松土,谁找到归谁,敲打一下,用衣服擦一擦就往嘴里塞,五哥常常挺着个大肚子,不知情的人以为他吃得太饱了撑的,其实是肚子里的虫太多的原因,有一次全家一起吃打虫药,五哥拉出来的竟然没有粪便,全白花花的虫子,我那时想,如果这些虫子拿来烤或油炸是不是也很也吃。
虽然时常吃打虫药,但虫子总也打不完,五哥给于蛔虫太多了,它们也许是太饿了,只好乱蹿,不时从鼻孔,嘴里钻出来,终于有一天钻进胆道,痛得満地打滚,差点玩完了,结果五哥命不该绝,硬靠打虫药活了下来。那种情形现在想起来浑身都会起鸡皮疙瘩,但在当时是一种很常见的情况。
吃成了我们要解决的主要问题,有时只有稀饭没有菜,我们就会盛好饭,端到外面去(反正每人只有一碗),再顺手拿走半张报纸(那时候讲政治,报纸可不缺),我们家不远的地方就是水产公司,门前常常晒着小鱼干,我会趁着没人,抓一把就跑,到没人的地方,用火点着报纸,把偷来的小鱼干放在上面烤一下,也不管是不是熟了,就着下饭,连小鱼上沾着的灰也吃得津津有味,一碗稀饭不到三分钟就吃完了,然后抹一下嘴边黑色的报纸灰,满足的回家。
三哥总是最有办法的,他常常放学的时候,顺便带点吃的回来,他要是晚加来我们就知道一定有好吃的了,兄弟总是围着他转,说是好吃的其实就是他总会到生产队的牛棚,把手抻进喂牛的桶里(那时我们这牛比人过得好,吃的总是番薯的叶、和根,还是煮熟的),捞出大一些的根块,带回家,然后偷偷分给我们兄弟几个,这可不能让大人知道,在他们眼里,这就是偷,不但要挨揍,还要写检讨,在家庭会议上宣读。
人如果真的饿了,为了可以吃一口,连人格和尊严都不要了,没有经历过的人是不能理解的。
除了吃以外,穿衣也是一个重要的生活目标,我从学一直到初中,基本上都是穿哥哥姐姐穿过的衣服,小的哥哥姐姐也是穿更大的哥哥姐姐的衣服,即使那个孩子难得做一件新衣服,妈妈也会报导衣[袖或裤腿做得长长的,以方便人长大了,可以不断的放长,报以我们的衣服就不可避免地在裤腿和衣袖上留下一圈一圈根据不同时期、深浅不一的痕迹,就好象少数民族的服装一样很有特色,只不过少数民族是一种刻意的装饰,而我们是无奈的表露,出来的效果自然也不一样,少数民族会被人称赞-----而我们只会引来哄笑。父亲下乡,有时带回来一个装过农药或尿素的袋子,我们兄弟几个看着那袋子,眼里全是渴望,都想妈妈用它给自己做件衣服,妈妈总是物尽其用,看那个孩子能尽量用完布料就给谁做衣服,我那时总不希望袋子太大。
妈妈把袋子拆开洗干净,晒干,然后花一毛钱买一小包和黑色的染料,放在水里煮开然后把布料染黑,挂起来晒干,再反复用水把布料漂清就成了一块好漂亮的布。只是穿的时间长了,经过多次的洗涤,自染的颜色会一点一点褪去,尿素、净重25公斤的字样就会显出来,常常成为同学们的笑料,幸好妈妈没有把这些字放在险要部位,要不刚好做在裤裆,出现净重25公斤字样,那一定会有不一般的麻烦。
尽管如此,这些化肥、农药袋子,仍是我们的最爱,因为用它们做成的衣服,才能是同一颜色的,我们其它的衣服常常是不同颜色、不同质地的布拼成的,虽然妈妈拼得很有心思,但还是一眼就可以看出绝对值不是为了装饰所为。我最喜欢的一件是用飞机拖靶做的衣服,,我们那靠近战斗机场,飞机练习射击是由一架飞机拖着一个布靶让后面的飞机打,有时打掉了就会有人捡了去做衣服,呵呵,我就有一件,那质地比现在法国的“蒙特娇”好多了,是真正的尼龙,穿一辈子也穿不破,而且永不褪色,虽然有点硬、也有点闷,也着实让我在同学,邻居面前眩耀了一番。
让我最开心的是,虽然 我们生活并不好,虽然我信有时吃不饱,也穿不好,而且我们不尽来自共同的父母,但我兄弟姐妹总是和和睦睦,比好多同父同母的亲兄弟还亲,这都因为我有一个好爸爸,一个有着海一样心胸,牛一样的干劲的好爸爸。
说是大家庭,其实也只有九个兄弟姐妹,比那个《家有七凤》电视剧里的家还多二个,但我们的家庭结构却要复杂得多,九个人中五个是属于妈妈的,三个属于爸爸,而我是属于爸爸妈妈共同的,因为我的父母是再婚,我本不是计划之中,但那时工具不好用,又没有什么娱乐,所以我才有幸于不经意之中来到这个世上。自小我就觉得是在人的背上和自行车的后架上长大的,我出世的时候文化大革命已经开始了,平时都是哥、姐背着我,武斗时是爸爸用自行车载着我逃往二十多公里的外婆家,由于兄弟姐妺多,爸爸总是二个载一程,放下走,然后回头再载两个,以加快前进的速度,我们一家人总可以走走歇歇,但爸爸却在不停的骑着那辆吱吱作响的自行车,不断来回的走,我们走了二十多公里,爸爸却走了四十多公里,现在想起来爸爸在夕阳中脸上没有汗,却浑身被汗水湿透的情景,我总是有种想哭的感觉。
妈妈是乡下农村的一个小学教师,爸爸是县城机关的干部,由于兄弟姐妹多,总是吃不饱,吃饱成了我们家最大的一件事,小时候,在哥哥姐姐的眼里,我是最幸福的孩子,记得每次分东西,我总是比他们多一点,一点有多少呢?打个比方说,这顿饭的菜是香肠,一根十五厘米象姆指粗的香肠,四个人分,我总是能比他们多分近一厘米,别小看一厘米,哥哥姐姐其实是馋得不得了,因为这一小段香肠是这一顿饭唯一的下饭菜。连青菜了没有,当然更不可能有什么汤,饭也常常是数得清米粒的稀饭。对待这一小段香肠我们可是格外的珍惜,都舍不得真吃,每次只是吮一下,饭吃完了(因为是定量,不能说吃饱,只能说吃完),这段香肠仍然是完整无缺,五哥哥说了这么一句:要是有一顿香肠吃个饱,真是天底下最大的幸福。
时候,我们都要做份内的工作,我七岁就要煮全家的饭,哥哥姐姐也要洗衣服,搞卫生,打小工,除我外星期天定额每人一篓柴草,没有完成的不能吃晚饭,有一次五哥不知是偷懒还是确实找不到柴草,傍晚回来的时候用树枝架在篓里,上面只是簿簿地铺了一层树叶,不幸被妈妈用脚一踩,全塌下去了,阴谋败露,结果当晚只能喝小半碗米汤,只有不停的喝水。
有一次我在路上捡了两毛钱,高兴得要命,那可是值两个鸭毛的钱,如果我知道是谁掉的,我会还给别人,但交给pol.ice他也找不到失主,我只好据为已有了,拿回家告诉哥哥姐姐,都高兴得要命,经过讨论,决定拿去买水果吃,我和哥哥到门前的国营果品公司,见到有架子上有好多水果,有苹果、梨、香蕉等,无论是颜色还是香味,都让我们喉咙产生的一丝丝清泉不断的往上涌,使我们看着对方,都不约而同地咽着,但我们都知道那架子上的水果我们是吃不起,或说从没舍得吃,于是我们硬生生地收回我们的贪婪的眼光,投向架子旁边的几个破筐,里面才是我们想要的,那里是一些没有烂完的水果,把烂的地方抠掉,洗一洗,分门别类一字摆着,那价格比架上的要便宜得多,尽管有些水果只烂剩了一条心,我们可不管,因为烂水果是论筐买的,而且买水果的那些人我们很熟两毛钱可以买一大筐了,商量了一下决定买苹果,因为除了好久没吃苹果外,还因为吃苹果不会象吃梨一样老要拉尿。我递我那个白发伯伯二毛钱,指指放烂水果的筐,他笑着走出来,指着一个装得滿滿的一筐,说这筐。行了吗?我和哥哥高兴得差点要跳起来,那一筐足有三十多斤,我们知道他是照顾我们,连连点头谢谢,告诉老伯伯,我们先把水果抬回去,再还筐,老伯伯说行,两兄弟抬着一大筐不断滴水的水果,兴奋地回到家,避开父母(我可不想父母问钱是那来的。那是招打),偷偷藏了起来,就等晚上人齐了就开餐。
晚上十点,等父母都睡了,我们偷偷起床,搬出那张大饭桌(我们家人多,饭桌当然也大),点起煤油灯,再提来一桶清水,先把那些烂水果洗干净,全堆在饭桌上,然后一人一把小刀,自削自吃,姐还轻轻的唱起了歌,在这个桌子上,没有父母是否相同之分,这是我到现在也感到我生在这样的家庭是幸福的原因,三十多斤的水果不到半个小时,基本只剩下了一堆果皮和削下来的垃圾,可还有人心有不甘用手东翻翻西翻翻,企图再找一些没吃干净的,却一无所获。
好的时光总是不长,清理完战场,我们睡下(我们都住在一个大房子),兴奋的声音此起彼伏,大家都很兴奋,没有一丝睡意,不久,响屁声代替了说话声,亲兄弟们就先后出去了(那时只有公厕),不用说大家也知道,去厕所,结果半夜时分,公厕内外全是我的兄弟姐妹白花花的屁股,场面颇为壮观,拉了一夜,大家都是眼塌脸白,三哥挣扎着抬起头,说了一句,拉也值。第二天喝了一肚子水后,竟也全部都不药而癒。
在我的印象中,最怕的东西就是塔糖--那种有很多种颜色的、造型也很漂亮的打虫药,刚开始吃的时候,觉得甜甜的,还不错,只是吃后有点恶心,吃多了就怕,宁愿让虫子吃也不想吃塔糖,却不得不常常吃。
究其原因,还是饥饿惹的祸,那时是见什么吃什么,可不管是不是卫生,与饥饿比起来,卫生简直就是微不足道。而最容易得到食物的地方就是刚收获过的番薯地,里面总有没收干净的番薯或大一些的根块,放学后总会跑到那里一边走一边用脚翻开松土,谁找到归谁,敲打一下,用衣服擦一擦就往嘴里塞,五哥常常挺着个大肚子,不知情的人以为他吃得太饱了撑的,其实是肚子里的虫太多的原因,有一次全家一起吃打虫药,五哥拉出来的竟然没有粪便,全白花花的虫子,我那时想,如果这些虫子拿来烤或油炸是不是也很也吃。
虽然时常吃打虫药,但虫子总也打不完,五哥给于蛔虫太多了,它们也许是太饿了,只好乱蹿,不时从鼻孔,嘴里钻出来,终于有一天钻进胆道,痛得満地打滚,差点玩完了,结果五哥命不该绝,硬靠打虫药活了下来。那种情形现在想起来浑身都会起鸡皮疙瘩,但在当时是一种很常见的情况。
吃成了我们要解决的主要问题,有时只有稀饭没有菜,我们就会盛好饭,端到外面去(反正每人只有一碗),再顺手拿走半张报纸(那时候讲政治,报纸可不缺),我们家不远的地方就是水产公司,门前常常晒着小鱼干,我会趁着没人,抓一把就跑,到没人的地方,用火点着报纸,把偷来的小鱼干放在上面烤一下,也不管是不是熟了,就着下饭,连小鱼上沾着的灰也吃得津津有味,一碗稀饭不到三分钟就吃完了,然后抹一下嘴边黑色的报纸灰,满足的回家。
三哥总是最有办法的,他常常放学的时候,顺便带点吃的回来,他要是晚加来我们就知道一定有好吃的了,兄弟总是围着他转,说是好吃的其实就是他总会到生产队的牛棚,把手抻进喂牛的桶里(那时我们这牛比人过得好,吃的总是番薯的叶、和根,还是煮熟的),捞出大一些的根块,带回家,然后偷偷分给我们兄弟几个,这可不能让大人知道,在他们眼里,这就是偷,不但要挨揍,还要写检讨,在家庭会议上宣读。
人如果真的饿了,为了可以吃一口,连人格和尊严都不要了,没有经历过的人是不能理解的。
除了吃以外,穿衣也是一个重要的生活目标,我从学一直到初中,基本上都是穿哥哥姐姐穿过的衣服,小的哥哥姐姐也是穿更大的哥哥姐姐的衣服,即使那个孩子难得做一件新衣服,妈妈也会报导衣[袖或裤腿做得长长的,以方便人长大了,可以不断的放长,报以我们的衣服就不可避免地在裤腿和衣袖上留下一圈一圈根据不同时期、深浅不一的痕迹,就好象少数民族的服装一样很有特色,只不过少数民族是一种刻意的装饰,而我们是无奈的表露,出来的效果自然也不一样,少数民族会被人称赞-----而我们只会引来哄笑。父亲下乡,有时带回来一个装过农药或尿素的袋子,我们兄弟几个看着那袋子,眼里全是渴望,都想妈妈用它给自己做件衣服,妈妈总是物尽其用,看那个孩子能尽量用完布料就给谁做衣服,我那时总不希望袋子太大。
妈妈把袋子拆开洗干净,晒干,然后花一毛钱买一小包和黑色的染料,放在水里煮开然后把布料染黑,挂起来晒干,再反复用水把布料漂清就成了一块好漂亮的布。只是穿的时间长了,经过多次的洗涤,自染的颜色会一点一点褪去,尿素、净重25公斤的字样就会显出来,常常成为同学们的笑料,幸好妈妈没有把这些字放在险要部位,要不刚好做在裤裆,出现净重25公斤字样,那一定会有不一般的麻烦。
尽管如此,这些化肥、农药袋子,仍是我们的最爱,因为用它们做成的衣服,才能是同一颜色的,我们其它的衣服常常是不同颜色、不同质地的布拼成的,虽然妈妈拼得很有心思,但还是一眼就可以看出绝对值不是为了装饰所为。我最喜欢的一件是用飞机拖靶做的衣服,,我们那靠近战斗机场,飞机练习射击是由一架飞机拖着一个布靶让后面的飞机打,有时打掉了就会有人捡了去做衣服,呵呵,我就有一件,那质地比现在法国的“蒙特娇”好多了,是真正的尼龙,穿一辈子也穿不破,而且永不褪色,虽然有点硬、也有点闷,也着实让我在同学,邻居面前眩耀了一番。
让我最开心的是,虽然 我们生活并不好,虽然我信有时吃不饱,也穿不好,而且我们不尽来自共同的父母,但我兄弟姐妹总是和和睦睦,比好多同父同母的亲兄弟还亲,这都因为我有一个好爸爸,一个有着海一样心胸,牛一样的干劲的好爸爸。