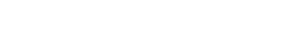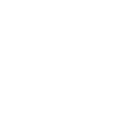在古代中国,阉割术的渊源是相当久远的。有证据表明,至迟在殷商时代就有了阉割男性生殖器的意识与行为。当时的阉割术可能是将阴茎与睾丸一并割除的,秦汉时期的阉割技术已较为完备,并已经注意到阉割手术后的防风、保暖、静养等护理措施。当时施行阉割的场所称为“蚕室”,《汉书·张安世传》颜师古注曰:“凡养蚕者,欲其温而早成,故为密室蓄火以置之。新腐刑亦有中风之患,需入密室乃得以全,因呼为蚕室耳。”大致相同的解释见于《后汉书·光武帝纪》李贤注,所谓“宫刑者畏风,须暖,作窨室蓄火如蚕室,因以名焉。 ”
古代的阉割方式大致有两种:一是“尽去其势”,即用金属利刃之类的器具将男性生殖器完全割除。《旧唐书·安禄山传》中曾记载一则阉割实例:
猪儿出契丹部落,十数岁事(安)禄山,甚黠慧。禄山持刃尽去其势,血流数升,欲死。禄山以灰火傅之,尽日而苏。
由此可以看出,阉割过程是相当残酷的,被阉割者会因失血过多或过于痛疼而长时间昏迷,止血消炎的措施也非常简单,只是“以灰火傅之”。
二是用利刃割开阴囊,剥出睾丸。用这一方法进行阉割显然并不需要完全割除生殖器官,但同样可以达到目的。洪迈所著《夷坚志》卷八对这一方法有所记载。另据记载,古代还有所谓的“绳系法”与“揉捏法”。前者是在男童幼小时,用一根麻绳从生殖器的“睾丸”根部系死,既不影响溺尿,却阻碍了生殖器的正常发育。久而久之,男童的生殖器便会失去功能。后者是在男童幼小时,由深谙此道之人每天轻轻揉捏其睾丸,渐渐适应后,再加大手劲,直至将睾丸捏碎。然而,专将睾丸割去或捏碎,如果是业已发育之人,尽管能够完全避免授精,但其性欲及淫乱宫廷的能力在一定时期内会依然存在,甚至有的人反会因此而更加强劲耐久。所以,古代的宦官都是采用“尽去其势”之法,将生殖器全部割除。
在古代相对落后的医疗技术条件下,阉割手术的死亡率是相当高的。明代天顺年间,镇守湖广贵州的太监阮让,一次精选了虏获的苗族幼童1565人,将他们统统阉割,准备悉数送呈朝廷。但由于手术太残酷及医疗技术条件太差,在阮让自阉割幼童到奏闻朝廷这短短的时间内,幼童疼死、病死者竟达329人。后来,阮让又重新买了一批幼童加以阉割,以补上死亡之数,送呈朝廷。阮让前后共计阉割幼童1894人,死亡率接近20%。如此集中而大量的死亡,显然同阉割手术失败或手术后的并发症有关。
历代古籍对阉割手术的具体情形大致上都记载得很是简略。清朝末年,一些来到中国的欧洲人对迥异于西方的中国宫廷文化产生了浓厚的兴趣,并较为详细地描述了当时的阉割手术情形。但这些描述多为道听途说,远不及清末宫廷宦官以切身经历为基础的回忆详细,其可*性也值得怀疑。据清末宦官回忆,北京城有两个赫赫有名的阉割世家,号称“厂子”:一是南长街会计司胡同的毕家;另一是地安门外方砖胡同的“小刀刘”。主持其事者都是得到朝廷认可的家族世传,六品顶戴,称“刀子匠”。两家据说各有绝招,但技艺绝不外露,只是父子相传。
净身需要选好季节,最好在春末夏初,气温不高不低,没有苍蝇蚊子,因为手术后约一个月下身不能穿衣服。净身者在手术前都需履行必要的手续,其中关键是订立生死文书,并需请上三老四少作为证明人,写明系自愿净身,生死不论,免得将来出麻烦吃官司。费用自然是要收取的,但净身者多来自贫困之家,一时或许拿不出很多银子,因而可以待进宫发迹后再逐年交纳。这些也需要在文书上写明白。但有两样东西是必须带着的,一是送给刀子匠的礼物,一般是一个猪头或一只鸡,外加一瓶酒。二是手术所用的物品,包括三十斤米、几篓玉米棒、几担芝麻秸及半刀窗户纸。其中,米是净身者一个月的口粮,玉米棒烧炕保暖用,芝麻秸烧成灰后用来垫炕,窗户纸则用来糊窗子,以免手术后受风。刀子匠要准备两个新鲜的猪苦胆、臭大麻汤和麦秆。猪苦胆有消肿止痛的作用,手术后敷在伤口处;臭大麻汤的功用很多,手术前喝一碗让人迷糊,起麻醉作用,手术后再喝,让手术者泻肚,以减轻小便的排泄量,保证手术成功;麦秆的功用不言自明,即手术后插入尿道。
手术过程中,除了主刀者外,一般还需三四名助手。被阉割者都需采用半卧姿势仰倒在床位上,几位助手将他的下腹及双股上部用白布扎紧、固定,然后有人负责按住其腰腹部,另外的人则用“热胡椒汤”清洗阉割部位,加以消毒。用于阉割的手术刀是一种呈镰状弯曲的利刃,据说是用金与铜的合金制成,可防止手术后感染,但使用时通常并没有特别的消毒措施,在火上烤一下,便算是消毒了。这一切完成后,主刀者即用镰状弯曲的利刃,对被阉割者的阴茎连同阴囊进行切除,通常分两步:第一步是割睾丸。在球囊左右各横割开一个深口子,把筋络割断以便把睾丸挤出来。这需要阉割者身子打挺,小肚子使劲往外鼓。待用全身的力气把睾丸挤出来,刀子匠会把片好的猪苦胆贴到球囊左右两边。
第二步是割阴茎。这需要相当高的技术,割浅了会留有余势,将来里面的脆骨会往外鼓出,就必须再挨第二刀,即宫里俗称的“刷茬”;如果割深了,将来痊愈后会往里塌陷,形成坑状,解小便时呈扇面状,一辈子不方便。宫里的太监十个有九个都有尿裆的毛病,这就是阉割的后遗症。阴茎割除后,要插上一根大麦秆,然后把另一个猪苦胆劈开,呈蝴蝶状地敷在创口上。据说也有的是用栓状白蜡针插入尿道,并用冷水浸湿的纸张,将伤口覆盖包扎。这大概是净身场所不同而出现的技术性差异。
古代的阉割方式大致有两种:一是“尽去其势”,即用金属利刃之类的器具将男性生殖器完全割除。《旧唐书·安禄山传》中曾记载一则阉割实例:
猪儿出契丹部落,十数岁事(安)禄山,甚黠慧。禄山持刃尽去其势,血流数升,欲死。禄山以灰火傅之,尽日而苏。
由此可以看出,阉割过程是相当残酷的,被阉割者会因失血过多或过于痛疼而长时间昏迷,止血消炎的措施也非常简单,只是“以灰火傅之”。
二是用利刃割开阴囊,剥出睾丸。用这一方法进行阉割显然并不需要完全割除生殖器官,但同样可以达到目的。洪迈所著《夷坚志》卷八对这一方法有所记载。另据记载,古代还有所谓的“绳系法”与“揉捏法”。前者是在男童幼小时,用一根麻绳从生殖器的“睾丸”根部系死,既不影响溺尿,却阻碍了生殖器的正常发育。久而久之,男童的生殖器便会失去功能。后者是在男童幼小时,由深谙此道之人每天轻轻揉捏其睾丸,渐渐适应后,再加大手劲,直至将睾丸捏碎。然而,专将睾丸割去或捏碎,如果是业已发育之人,尽管能够完全避免授精,但其性欲及淫乱宫廷的能力在一定时期内会依然存在,甚至有的人反会因此而更加强劲耐久。所以,古代的宦官都是采用“尽去其势”之法,将生殖器全部割除。
在古代相对落后的医疗技术条件下,阉割手术的死亡率是相当高的。明代天顺年间,镇守湖广贵州的太监阮让,一次精选了虏获的苗族幼童1565人,将他们统统阉割,准备悉数送呈朝廷。但由于手术太残酷及医疗技术条件太差,在阮让自阉割幼童到奏闻朝廷这短短的时间内,幼童疼死、病死者竟达329人。后来,阮让又重新买了一批幼童加以阉割,以补上死亡之数,送呈朝廷。阮让前后共计阉割幼童1894人,死亡率接近20%。如此集中而大量的死亡,显然同阉割手术失败或手术后的并发症有关。
历代古籍对阉割手术的具体情形大致上都记载得很是简略。清朝末年,一些来到中国的欧洲人对迥异于西方的中国宫廷文化产生了浓厚的兴趣,并较为详细地描述了当时的阉割手术情形。但这些描述多为道听途说,远不及清末宫廷宦官以切身经历为基础的回忆详细,其可*性也值得怀疑。据清末宦官回忆,北京城有两个赫赫有名的阉割世家,号称“厂子”:一是南长街会计司胡同的毕家;另一是地安门外方砖胡同的“小刀刘”。主持其事者都是得到朝廷认可的家族世传,六品顶戴,称“刀子匠”。两家据说各有绝招,但技艺绝不外露,只是父子相传。
净身需要选好季节,最好在春末夏初,气温不高不低,没有苍蝇蚊子,因为手术后约一个月下身不能穿衣服。净身者在手术前都需履行必要的手续,其中关键是订立生死文书,并需请上三老四少作为证明人,写明系自愿净身,生死不论,免得将来出麻烦吃官司。费用自然是要收取的,但净身者多来自贫困之家,一时或许拿不出很多银子,因而可以待进宫发迹后再逐年交纳。这些也需要在文书上写明白。但有两样东西是必须带着的,一是送给刀子匠的礼物,一般是一个猪头或一只鸡,外加一瓶酒。二是手术所用的物品,包括三十斤米、几篓玉米棒、几担芝麻秸及半刀窗户纸。其中,米是净身者一个月的口粮,玉米棒烧炕保暖用,芝麻秸烧成灰后用来垫炕,窗户纸则用来糊窗子,以免手术后受风。刀子匠要准备两个新鲜的猪苦胆、臭大麻汤和麦秆。猪苦胆有消肿止痛的作用,手术后敷在伤口处;臭大麻汤的功用很多,手术前喝一碗让人迷糊,起麻醉作用,手术后再喝,让手术者泻肚,以减轻小便的排泄量,保证手术成功;麦秆的功用不言自明,即手术后插入尿道。
手术过程中,除了主刀者外,一般还需三四名助手。被阉割者都需采用半卧姿势仰倒在床位上,几位助手将他的下腹及双股上部用白布扎紧、固定,然后有人负责按住其腰腹部,另外的人则用“热胡椒汤”清洗阉割部位,加以消毒。用于阉割的手术刀是一种呈镰状弯曲的利刃,据说是用金与铜的合金制成,可防止手术后感染,但使用时通常并没有特别的消毒措施,在火上烤一下,便算是消毒了。这一切完成后,主刀者即用镰状弯曲的利刃,对被阉割者的阴茎连同阴囊进行切除,通常分两步:第一步是割睾丸。在球囊左右各横割开一个深口子,把筋络割断以便把睾丸挤出来。这需要阉割者身子打挺,小肚子使劲往外鼓。待用全身的力气把睾丸挤出来,刀子匠会把片好的猪苦胆贴到球囊左右两边。
第二步是割阴茎。这需要相当高的技术,割浅了会留有余势,将来里面的脆骨会往外鼓出,就必须再挨第二刀,即宫里俗称的“刷茬”;如果割深了,将来痊愈后会往里塌陷,形成坑状,解小便时呈扇面状,一辈子不方便。宫里的太监十个有九个都有尿裆的毛病,这就是阉割的后遗症。阴茎割除后,要插上一根大麦秆,然后把另一个猪苦胆劈开,呈蝴蝶状地敷在创口上。据说也有的是用栓状白蜡针插入尿道,并用冷水浸湿的纸张,将伤口覆盖包扎。这大概是净身场所不同而出现的技术性差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