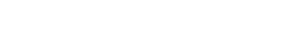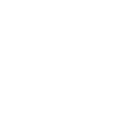[font=楷体_GB2312]《门徒》:香港兵贼角力兜售大陆主导意识…[/font]

听上去,“门徒”两字极富江湖意境。在武侠文化中,各路武林门派通过收徒纳弟来延续“门脉”。香港黑帮警匪电影中,更是随处可以看到收小弟、拜关爷的段子,打打杀杀从来少不了门徒的身影。吴镇宇饰演的“血门徒”对着自己脑袋扣动板机的宿命与悲情还在心头萦绕,尔东升便带着自己的“门徒”跃入观众的视野。
尔东升算得上香港影界的一个多面手,在警匪类型片方面也颇有造诣,《旺角黑夜》曾在香港电影金像奖上大出风头。《门徒》延续着《旺角黑夜》里的警匪角逐,又不同于传统的警匪对峙,通过“毒品恐怖论”注入浓厚的社会思想意味。影片以昆哥和阿力之间的师徒关系表现出毒品制作、交易的内幕,构成警匪角力的主线;又以阿芬夫妇的吸毒惨剧表现出毒品的巨大危害,构成叙事的辅线。这种脱离原有兵贼游戏套路的故事,赋予《门徒》一些香港警匪片少有的社会思想深度,观众也多了些观影的新鲜感。然而,这种深度与新鲜的背后隐藏着不少深层因素。仔细分析,它所体现的不是香港电影人更为广阔的创作视野和灵活多变的创作类型,也不是香港电影人开拓新的空间、突破旧有窠臼的创新努力,本质上是香港电影人对于大陆主导思想的迎合,意味着港片特色的削减和迷失前奏。
自《无间道》后,香港警匪片在故事性上有了一个极大的转变,“卧底风”愈演愈烈,到了去年王晶监制的《卧虎》时已达“三万警员做卧底”的空前盛景,警方全方位深层次地渗入香港的黑社会。在香港电影“黑帮教父”杜棋峰的《黑社会》及续作《以和为贵》中,警方能力也足以一手遮天,社团秩序受到严峻挑战,帮会规则被逐渐改写,像《暗战》、《高度戒备》这样斗智斗勇的兵贼角力基本已无望重现香江银幕。《门徒》的警匪创作立意遵循的是近来年蔚然成风的“卧底”路线,作为“门徒”的核心主角阿力的真正身分是警方“卧底”。虽然片中数次直白地说出“门徒”二字,但电影没有能够提供片名《门徒》包含的江湖意境。既然已经有表现“卧虎行动”的《卧虎》在前,将讲述卧底故事的《门徒》改名为《卧底》也未尝不可,俗是俗了点,但更加贴近故事内容。
现在的香港电影为了谋求通过内地审检和公映,在商业利益的驱使下,社会说教气息越来越浓。一部电影包含一些社会正面的宣教本无可厚非,关健是要做到不要伤害最为核心的剧情和特色。《门徒》通过古天乐和张静初扮演的一对吸毒夫妇,将毒品的危害以慑人的镜头展现出来,包括多处出现的惊悚音乐和疾行翻滚的阴云画面,还有首尾呼应、以独白形式道出的“究竟是空虚恐怖还是毒品恐怖”的疑问,将毒品危害作了一再地深度提升。从这点来看,把《门徒》看作是一部寓意深刻、令人深思的“戒毒教育片”也是很有道理的。
很早以来,香港电影就有“卧底”元素,《风虎风云》中的高秋便是其中代表。林岭东在警方卧底与黑道劫匪的对决中,通过生死角逐构建出一个情义动人的江湖世界,周润发和李修贤以精湛的演技注释了兵贼的另类关系,令不少男儿热血沸腾。《门徒》也有意演绎兵贼的情义关系,在日常生活上,阿力和昆哥有几份情同手足的兄弟情义;在泰国金三角毒品基地里,昆哥试探阿力的段落具有很强的警匪斗智斗狠的色彩。问题是编导过于强烈的社会警世说教严重淡化了这种江湖情义,阿力对自己背叛昆哥并无太大的内心愧疚,认为一切都是设计的局数,一切都是自然而然的事情,致使最后昆哥的自杀也就没有了打动人心的力量。
对于警察抓贼的动机,《门徒》与《龙虎风云》也是完全不同。在林岭东的思路下,作为卧底的警察是凭着“天职”来破坏犯罪行动。尔东升没有忘记卧底的“天职”的底线,阿力及时将昆哥集团的情况向上司反馈。但警察抓获犯罪分子的动因,已由警察的“天职”让位于“毒品危害”及其引发的人性良知。在剧情的发展中,让阿力决定将昆哥绳之以法的力量,不是他作为“兵”的身份,而是阿芬因吸毒而死的事实。这就是影片中,阿力看见一群老鼠在阿芬身上乱爬,目瞪口呆掩面嘶叫,镜头淡出切换后,一张拘捕令将昆哥带进了警局。
营建风起云涌、残暴无常的江湖向来都是香港电影的强项。《门徒》在此方面却没任何过人之处,警匪对决显得虎头蛇尾,很多地方浅尝辄止、难以自圆其说。开头一段,警察追踪贩毒分子的跟踪戏,从场面调动、画面剪辑到配乐,都是典型的港片风韵,快速切换中表现出紧迫、激烈的兵贼智力游戏。电影的主体部分,除了警察摧毁毒品工厂和泰国金三角毒品基地两段之外,基本上没有构建出真正警匪江湖世界。阿力和小姨之间的男女关系是展现江湖的一个要素,电影只是蜻蜓点水式的涉猎,没有丝毫的灵魂揭示,实在是可有可无。对昆哥和阿力这两个毒品集团的“大人物”的交待,也是非常含糊不清和缺乏统一性。从警方破案的选择来看,昆哥贩毒集团具有大财团(社团)的地位派头,控制着香港大半的毒品市场,有实力出入泰国的豪华别墅。但在开头,作为如此集团的龙头老大的昆哥生病了住的是公共医院,他的得力助手居然买不起房子住在贫民窟,这在以往的警匪片里都是不可能的事。
我们自然可以说,《门徒》有毒品危害和兵贼角力两方面的剧情内容。但问题的关键在于,影片对本是香港导演驾轻就熟的警匪部分表现得平平淡淡,毒品交易等黑道内幕只是轻描淡写地交待,反而在香港电影并不擅长的社会宣教的思想性上做得相当成功。为什么会出现这种反常现象呢?我想,至少可以从演员表演和内地参与创作两方面来分析。
《门徒》对于社会宣教思想的成功表达与演员出色的表演关系密切。从《花腰新娘》中活泼可爱的彝族乡姑,到《门徒》中竭斯底里的吸毒女郎,对两个天壤之别的角色,张静初的表演丝毫没有做作的痕迹,尤其是注射毒品前后入魔虐待式的强烈反应让人叹服,难怪导演赞叹:“就是张曼玉有机会和她对戏的话,也得要打起精神来”。古天乐饰演的吸毒男子,保持着《河东狮吼》、《宝贝计划》的喜剧本色,一方面起到了制造轻松观影气氛的娱乐效果,另一方面,满口脏丑的金牙和泯灭良知的邋遢形象十分切合“瘾君子”的身份,与阿芬一起将毒品摧毁灵魂的恐怖感呈现出来。
从制片、出品、策划来看,《门徒》由大陆与香港合作拍摄,在片尾的特别感谢栏里劈头盖脸地写着“黄建新导演”的字样。剧本乃一剧之本,“剧本顾问”黄建新很大程度上左右了电影的成败得失。影片结尾设计充分说明了这一点。按照香港警匪片的经典叙事模式,在昆哥自杀之后,故事完全可以戛然而止,留给观众江湖风雨无常的体验。但是,编导并没有这么做,而是在此之后让背叛“大哥”的“门徒”毫无愧疚地继续担当“卧底”,让“瘾君子”伏法获得重新做人的机会,让无人照料的小女孩得到家庭般的温暖,让天真无邪的孩子将“烟具”丢进纸娄,让政府主导下的正义力量和人性光环覆盖全部,这些恰恰是大陆主流导演们的“看家本领”。
《门徒》本是警匪题材,但它的故事在《龙虎风云》、《龙在边缘》等珠玉面前基本失去了港片的品质与亮点,留给观众的反到是“毒品恐怖论”的警世说教。就电影的特色来说,这无疑是香港电影和香港导演的迷失,是大陆主导思想和大陆导演的成功。简言之,合拍的《门徒》是香港电影人以自己擅长的题材完成一次对大陆主导思想的逢迎与展现。
2005年香港电影金像奖举行前,曾志伟先生就坦言:“香港电影会慢慢淡出人们的记忆” 。他认为,香港电影、内地电影的界限将会越来越模糊,香港电影与内地电影将融合为一,今后只有”中国电影“这一说法。现在看来,这绝对不是危言耸听而是客观的发展必然。从《九龙冰室》到《天行者》,从《江湖》到《阿嫂传奇》再到《门徒》,我们看到了太多的正义力量、弃恶就善和从良说教,那种我们熟悉的亦正亦邪、忠奸难辨、血腥暴力的江湖渐渐地变味、淡化、消亡。同样是警匪题材,像《杀破狼》这样纯粹的港式经典很可能成为绝唱,《英雄本色》、《野兽刑警》、《高度戒备》的时代再也不会重现了。

听上去,“门徒”两字极富江湖意境。在武侠文化中,各路武林门派通过收徒纳弟来延续“门脉”。香港黑帮警匪电影中,更是随处可以看到收小弟、拜关爷的段子,打打杀杀从来少不了门徒的身影。吴镇宇饰演的“血门徒”对着自己脑袋扣动板机的宿命与悲情还在心头萦绕,尔东升便带着自己的“门徒”跃入观众的视野。
尔东升算得上香港影界的一个多面手,在警匪类型片方面也颇有造诣,《旺角黑夜》曾在香港电影金像奖上大出风头。《门徒》延续着《旺角黑夜》里的警匪角逐,又不同于传统的警匪对峙,通过“毒品恐怖论”注入浓厚的社会思想意味。影片以昆哥和阿力之间的师徒关系表现出毒品制作、交易的内幕,构成警匪角力的主线;又以阿芬夫妇的吸毒惨剧表现出毒品的巨大危害,构成叙事的辅线。这种脱离原有兵贼游戏套路的故事,赋予《门徒》一些香港警匪片少有的社会思想深度,观众也多了些观影的新鲜感。然而,这种深度与新鲜的背后隐藏着不少深层因素。仔细分析,它所体现的不是香港电影人更为广阔的创作视野和灵活多变的创作类型,也不是香港电影人开拓新的空间、突破旧有窠臼的创新努力,本质上是香港电影人对于大陆主导思想的迎合,意味着港片特色的削减和迷失前奏。
自《无间道》后,香港警匪片在故事性上有了一个极大的转变,“卧底风”愈演愈烈,到了去年王晶监制的《卧虎》时已达“三万警员做卧底”的空前盛景,警方全方位深层次地渗入香港的黑社会。在香港电影“黑帮教父”杜棋峰的《黑社会》及续作《以和为贵》中,警方能力也足以一手遮天,社团秩序受到严峻挑战,帮会规则被逐渐改写,像《暗战》、《高度戒备》这样斗智斗勇的兵贼角力基本已无望重现香江银幕。《门徒》的警匪创作立意遵循的是近来年蔚然成风的“卧底”路线,作为“门徒”的核心主角阿力的真正身分是警方“卧底”。虽然片中数次直白地说出“门徒”二字,但电影没有能够提供片名《门徒》包含的江湖意境。既然已经有表现“卧虎行动”的《卧虎》在前,将讲述卧底故事的《门徒》改名为《卧底》也未尝不可,俗是俗了点,但更加贴近故事内容。
现在的香港电影为了谋求通过内地审检和公映,在商业利益的驱使下,社会说教气息越来越浓。一部电影包含一些社会正面的宣教本无可厚非,关健是要做到不要伤害最为核心的剧情和特色。《门徒》通过古天乐和张静初扮演的一对吸毒夫妇,将毒品的危害以慑人的镜头展现出来,包括多处出现的惊悚音乐和疾行翻滚的阴云画面,还有首尾呼应、以独白形式道出的“究竟是空虚恐怖还是毒品恐怖”的疑问,将毒品危害作了一再地深度提升。从这点来看,把《门徒》看作是一部寓意深刻、令人深思的“戒毒教育片”也是很有道理的。
很早以来,香港电影就有“卧底”元素,《风虎风云》中的高秋便是其中代表。林岭东在警方卧底与黑道劫匪的对决中,通过生死角逐构建出一个情义动人的江湖世界,周润发和李修贤以精湛的演技注释了兵贼的另类关系,令不少男儿热血沸腾。《门徒》也有意演绎兵贼的情义关系,在日常生活上,阿力和昆哥有几份情同手足的兄弟情义;在泰国金三角毒品基地里,昆哥试探阿力的段落具有很强的警匪斗智斗狠的色彩。问题是编导过于强烈的社会警世说教严重淡化了这种江湖情义,阿力对自己背叛昆哥并无太大的内心愧疚,认为一切都是设计的局数,一切都是自然而然的事情,致使最后昆哥的自杀也就没有了打动人心的力量。
对于警察抓贼的动机,《门徒》与《龙虎风云》也是完全不同。在林岭东的思路下,作为卧底的警察是凭着“天职”来破坏犯罪行动。尔东升没有忘记卧底的“天职”的底线,阿力及时将昆哥集团的情况向上司反馈。但警察抓获犯罪分子的动因,已由警察的“天职”让位于“毒品危害”及其引发的人性良知。在剧情的发展中,让阿力决定将昆哥绳之以法的力量,不是他作为“兵”的身份,而是阿芬因吸毒而死的事实。这就是影片中,阿力看见一群老鼠在阿芬身上乱爬,目瞪口呆掩面嘶叫,镜头淡出切换后,一张拘捕令将昆哥带进了警局。
营建风起云涌、残暴无常的江湖向来都是香港电影的强项。《门徒》在此方面却没任何过人之处,警匪对决显得虎头蛇尾,很多地方浅尝辄止、难以自圆其说。开头一段,警察追踪贩毒分子的跟踪戏,从场面调动、画面剪辑到配乐,都是典型的港片风韵,快速切换中表现出紧迫、激烈的兵贼智力游戏。电影的主体部分,除了警察摧毁毒品工厂和泰国金三角毒品基地两段之外,基本上没有构建出真正警匪江湖世界。阿力和小姨之间的男女关系是展现江湖的一个要素,电影只是蜻蜓点水式的涉猎,没有丝毫的灵魂揭示,实在是可有可无。对昆哥和阿力这两个毒品集团的“大人物”的交待,也是非常含糊不清和缺乏统一性。从警方破案的选择来看,昆哥贩毒集团具有大财团(社团)的地位派头,控制着香港大半的毒品市场,有实力出入泰国的豪华别墅。但在开头,作为如此集团的龙头老大的昆哥生病了住的是公共医院,他的得力助手居然买不起房子住在贫民窟,这在以往的警匪片里都是不可能的事。
我们自然可以说,《门徒》有毒品危害和兵贼角力两方面的剧情内容。但问题的关键在于,影片对本是香港导演驾轻就熟的警匪部分表现得平平淡淡,毒品交易等黑道内幕只是轻描淡写地交待,反而在香港电影并不擅长的社会宣教的思想性上做得相当成功。为什么会出现这种反常现象呢?我想,至少可以从演员表演和内地参与创作两方面来分析。
《门徒》对于社会宣教思想的成功表达与演员出色的表演关系密切。从《花腰新娘》中活泼可爱的彝族乡姑,到《门徒》中竭斯底里的吸毒女郎,对两个天壤之别的角色,张静初的表演丝毫没有做作的痕迹,尤其是注射毒品前后入魔虐待式的强烈反应让人叹服,难怪导演赞叹:“就是张曼玉有机会和她对戏的话,也得要打起精神来”。古天乐饰演的吸毒男子,保持着《河东狮吼》、《宝贝计划》的喜剧本色,一方面起到了制造轻松观影气氛的娱乐效果,另一方面,满口脏丑的金牙和泯灭良知的邋遢形象十分切合“瘾君子”的身份,与阿芬一起将毒品摧毁灵魂的恐怖感呈现出来。
从制片、出品、策划来看,《门徒》由大陆与香港合作拍摄,在片尾的特别感谢栏里劈头盖脸地写着“黄建新导演”的字样。剧本乃一剧之本,“剧本顾问”黄建新很大程度上左右了电影的成败得失。影片结尾设计充分说明了这一点。按照香港警匪片的经典叙事模式,在昆哥自杀之后,故事完全可以戛然而止,留给观众江湖风雨无常的体验。但是,编导并没有这么做,而是在此之后让背叛“大哥”的“门徒”毫无愧疚地继续担当“卧底”,让“瘾君子”伏法获得重新做人的机会,让无人照料的小女孩得到家庭般的温暖,让天真无邪的孩子将“烟具”丢进纸娄,让政府主导下的正义力量和人性光环覆盖全部,这些恰恰是大陆主流导演们的“看家本领”。
《门徒》本是警匪题材,但它的故事在《龙虎风云》、《龙在边缘》等珠玉面前基本失去了港片的品质与亮点,留给观众的反到是“毒品恐怖论”的警世说教。就电影的特色来说,这无疑是香港电影和香港导演的迷失,是大陆主导思想和大陆导演的成功。简言之,合拍的《门徒》是香港电影人以自己擅长的题材完成一次对大陆主导思想的逢迎与展现。
2005年香港电影金像奖举行前,曾志伟先生就坦言:“香港电影会慢慢淡出人们的记忆” 。他认为,香港电影、内地电影的界限将会越来越模糊,香港电影与内地电影将融合为一,今后只有”中国电影“这一说法。现在看来,这绝对不是危言耸听而是客观的发展必然。从《九龙冰室》到《天行者》,从《江湖》到《阿嫂传奇》再到《门徒》,我们看到了太多的正义力量、弃恶就善和从良说教,那种我们熟悉的亦正亦邪、忠奸难辨、血腥暴力的江湖渐渐地变味、淡化、消亡。同样是警匪题材,像《杀破狼》这样纯粹的港式经典很可能成为绝唱,《英雄本色》、《野兽刑警》、《高度戒备》的时代再也不会重现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