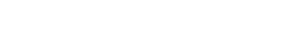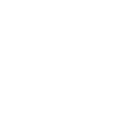[font=楷体_GB2312]艳若桃花[/font]
她说夜是她的颜色。
遇见她是在新天地某个酒吧的露天座,夏天的夜晚,我百无聊赖地耗掉一包七星,正在喝第三杯不加冰块的龙舌兰酒,这玩意儿干喝味道简直同酒精无异。十点刚过,整个新天地的人气已经开始疯长,到处满座,老外们拿着杯子在座位间穿梭,露天座旁也三三两两站着闲谈或等待的人。
我在心里暗自决定,要是第三次看到那个女孩经过,我就请她喝一杯。
这么想不仅是因为她很美。你很容易在新天地遇见美女,其概率远远超过在这个城市的任何一个角落。别问我这是为什么,你只要来这里坐过就知道了,当你闻到这里混合着烟味、香水味、酒精味以及人们的各种莫名欲望和无聊感的气味后,你就知道为什么我喜欢坐在新天地的露天座观赏各色行人了。
尽管看了这么多人,但这个在十分钟之内两次经过我眼前的女孩子,总有某种让人牵动的地方。
她当然是穿着黑色,就像很多女孩子一样,在这样明亮的夜色里,用比夜更深的颜色来隐藏自己。我注意到她,是因为她明媚夺人的眼神,还有,她两次闯入我的视线时,都携着不同的女子。那两个妆容精致的女子在她的映照下,不能不显出花容失色的秋香式对比。
有那么多的人从我眼前经过,我几乎快要失去耐心了。这就像是一个狩猎游戏,只不过被猎者毫不知情。
她再次出现在我面前时,我刚刚喝完杯底的酒。时间正好够我走到她面前,我尽量从容不迫地问道,能不能请她喝杯酒。
没有迟疑,她笑了,并且点头。笑容一如我想象般甜美。
在这么短短几秒钟里,我的座位已经被人占领了。我只好和她走进嘈杂的室内。
我们找了个墙角的高脚桌放上酒杯,没有位子,只能站着。这个位置能看到歌手的侧脸,满室冰蓝色的灯光,她的脸就在这样的光线里凄迷地美艳着。
我们喝酒,只是喝酒,没有交谈。她很快地喝完了杯子里的伏特加和橙汁的混合物,冲我嫣然一笑。
谢谢你的酒,她说。不过很可惜我要回去工作了。她的声音沙哑,没有一丝做作的意味。
你在这里工作?
对。
那你什么时候下班?
我不知道。可能会很晚。
没关系,那我等你。
她用一只手把头发向后掠了一下,看了我一眼。然后她说,知道吗,这些话我听得多了,不过我还是第一次听到这样的话从一个孩子的嘴里说出来。
说完这些话,她就走了。留下我一个人看着蓝色灯光下模糊的人群。我开始等,因为我想告诉她我不是个孩子,我觉得自己已经老了。而且她没说不让我等。
她也没说她会回来。
那天她回来的时候是午夜两点。有的酒吧打烊了,有的还没有。人群逐渐退却。我的胃有灼烧的感觉,因为我不负责任地灌了那么多酒的缘故。忘记是哪个朋友说的了,过了二十五岁就应该学会爱惜自己,可惜我并不是常常能够做到。
我所在的酒吧开始清场,围着黑围裙的water跑过来问我是否还要点酒。我摇摇头,正准备走,肩上突然感觉到轻柔的压力。一转头,正看见她的笑容。也许是因为酒精的作用,我竟然有些许的恍惚,以为这不过是自己的幻觉。直到她开始说话。
你没走。她说。
我说过要等你的。
如果我不回来呢。
那我明天还会再来。
这样做有什么意义呢。
至少可以看见你。我笑笑,说,我没别的意思,只是想看看你。
她注视了我一秒钟,然后说,这里的人都叫我桃花。
我说,别人都叫我飞鸟。
那天后来我们去了新天地附近的一个绿地里聊天。那个绿地有一个人造湖,晚上沿着湖开了一溜灯,湖边几乎无人,很安静。她从酒吧买了一瓶杰克丹尼,又拿了两个杯子——她好像和这里的酒保很熟——我们就坐在湖边的台阶上喝酒聊天,那天我也许喝了这辈子最多的酒,后来我醉了,很可能吐过,但第二天起来的时候脑子几乎一片空白。
我只依稀记得我和她讲了阮宁的事。阮宁是我在大学时代的女友,大学毕业后我们就各奔东西不再联系,彼此似乎是刻意地维持着生疏的距离,装作什么也不记得。人有时候就是这么自欺欺人。我曾经那么地爱她,在每一个寒冷的早晨为她从食堂买好热气腾腾的早饭,秋天里我们骑自行车去郊外,我拍了那么多她的相片,在铺满红叶的小径。所有的亲吻和誓言,所有的肌肤温暖,终于在现实的空气中变淡,淡得像一张写满字却在洗衣机里被揉成一团的情书,连落款和抬头都辨认不清。
我不知道为什么要和这个刚刚认识的漂亮女孩子说这些。我连她姓什么都不知道。我只知道她叫桃花,该死的网络时代,每个人都习惯了用若干个ID,每一张面具的背后,其实都是无聊疲倦的面孔。我一边想着这些,一边絮絮叨叨地和她说阮宁,其实只是因为我醉了。
我记得自己上一次喝醉是什么时候,那是在大学毕业前的同学聚会上。我不是轻易会让自己陷入失控状态的人。太冷静,有时只是一种悲哀。
我从酒醉中醒过来后的第一件事,就是看现在几点钟。下午两点。看完后才想起来今天是星期六,不用上班,于是决定继续睡。但见鬼的是我清醒无比,甚至没有宿醉后应有的头痛,失去了自暴自弃的资格,我只好爬起来打扫房间。
这时才看到桌上有张纸。上面写着,钥匙在你的包里,我擅自取了开门,已经放回去了。地址是你自己和出租车司机说的。豆浆油条是我买的。不用道谢。
字写得很有力,间距很开,是出自利落性格的人之手。
我又重新看了一遍那张字条,然后开始坐在桌前吃豆浆油条。豆浆已经冷了,油条也已经发软,但对于饥肠辘辘的我来说是无上的美味。很久没有吃这些东西的习惯了,早餐我通常都是牛奶加几片饼干对付过去就算。想到那个一袭黑衣的名叫桃花的女孩子排在清晨买菜归来的阿姨爷叔中买早饭的场景,我不禁微笑。
五点多的时候接到明子打来的一个电话。他说,今天晚上有聚会,问我去不去。
我有事。我对他说,不去了。再说去了也没什么意思。
是不是因为有不想看到的人。他在电话的那一头轻笑道。
我可没有什么不想看到的人。我对着话筒说,我才没那么无聊。不玩这种新伤旧恨的把戏。我是真的有事。
那就算了。他说,你可不要硬撑哦,实在受不了可以到我这里来哭泣嘛。我的肩膀也可以偶尔借你一用的。
我笑起来。他不会知道,我已经畅快淋漓地哭过了,在一个陌生女子的肩头。依稀记起她的香水,陌生的绮艳的味道。
挂上明子的电话,我看着窗外发了一会儿呆。分手是一件很平常的事,无非是各奔东西罢了,最初的时候会有些不适,但说真的有什么不会成为过去呢。我知道自己不是因为怕看见萱而不敢出现,我只是觉得疲倦,就像野兽厌倦了它的角逐。她曾经说过将爱我至永远,她们都这样重复着同样的话语,最终却都离我而去。只留下回忆,就像债务一样让人喘不过气。
但至少生活中还有值得期待的事,我知道晚上我可以在新天地看见桃花。
她今天穿的仍是黑色。不同的黑,质地和款式造就了她的千变万化。如果说昨晚她的美艳吸引了我,那么今晚她的温婉则更加动人。
头痛吗。她款款走到我跟前问我。我坐在昨天相识的酒吧吧台一角,像个好孩子一样喝着一杯不含酒精的干姜水。
状态好极了。我说。谢谢你昨天送我回家。
我不是说过不用道谢了吗,她淡然道。她拿出烟,我顺手帮她点上。她低头对烟的时候,睫毛像蝴蝶的翅膀一样轻颤,让人有亲吻的欲望。她真是美。我注视她,心里在想,这样的女孩子,一定早已被某个人拥有。但这也没什么值得羡慕的,女孩子让人头痛的程度往往与其美丽程度成正比。
你今天不用去上班吗。她在我身旁坐了足足有一刻钟后,我问她。
我今天休息。她转动着手里的红酒杯子看杯壁流转的血红颜色,说。
周六休息岂不是太可惜了,周六生意会比较好。
你怎么知道我做的是什么生意,你又怎么知道周六生意好不好。她笑起来。
我知道的。我看着她的眼睛说,你做的是人的生意。
你真聪明,她喝了一口酒,说,你不如直白地说更恰当些,我确实是个卖家。而且我不仅卖自己,也卖别人。
我的脑海中顿时闪出三个字,但我不想把这么伧俗的字眼和她对号入座。于是我只是喝了一大口干姜水,彻底的冰凉使得喉咙一阵麻木。
你现在想做什么,她问,我今天有空,陪你散心。
我不需要散心。我说,不过谢谢你陪我。你想不想跳舞?
在这里?
我转头四顾,周围的人群几乎让人分辨不出自己所在的国度,我看了看高大傲慢肥胖的白种男人和他们身边笑容暧昧的黑发女人,对她说,不在这里,我领你去一个地方。
当我和桃花一同走进那家酒吧的时候,我知道自己多少带有报复的意味。她也确实达到了我所预期的效果,四下投射过来的目光,带有各种不同的含义。我走到明子旁边的位子让她坐下,明子和她的女友同时复杂地看了我一眼。然后明子对酒吧的主人老克说,给飞鸟来瓶百威。
桃花说,我要一杯红粉佳人,不要加蛋清。自从走进这里,她的神色没有丝毫变化,仿佛一切都顺理成章。
老克也对她露出一点惊艳的表情,或许只是出于虚伪。这不重要。每个来这里的人都有着自己黑暗的一面,重要的是我们可以在这里找到安慰和认同。
老克把酒端上来的间隙,明子低声问我,在哪里认识她的。
新天地,我说。
那么她是不是……?明子略带惊讶地说。
我不知道。这不重要吧。我说。我们只是来跳舞的。
我们只是来跳舞的。因为在这里跳舞不会有别人特殊的眼光来打扰。我拉着桃花的手走入中间的舞池,音乐强劲地包围着我,我开始在音乐中摆动身体,她的面容在镭射光束的闪烁中忽隐忽现。
不知何时,音乐变成了蓝调。我想都没想就环住了她的腰。很柔软。她的幽香划过我的脸。
你用的是什么香水。我低声在她耳旁问。
这支香水的名字叫作诱惑。她说,你以前的女朋友今天来了吗。
你指哪一个?我问。
最近分手的那一个。
我不记得自己是否告诉过她有关萱的事情,不过这已经不重要了。
她在角落里,我说,穿白衣的那个。
我拥着她慢慢旋转,以使她看到萱。萱并没有看我。她在和身旁的一个女孩子笑着交谈,也许她一开始就没看到我,也许她看到了却装作没看到,又或许她看到了但是无所谓。我还记得第一次在这里邂逅她的情景,那时她也是穿白衣,她的眼睛在夜色里明亮又温暖。我也记得在某个清晨,她坐在床头递给我一碗热粥。三百多个日夜。一年。然而一切说变就变。她走的时候没有解释这是为什么。我也不想听到任何所谓的解释。
我想我并不是没有留恋,但我已经学会将一切看得很淡,就像此刻,我看到夜色里的萱,心里只有一片空虚的茫然。也许是因为已经忘记了如何疼痛。爱一个人很容易,忘却也很容易。我的面前是个美丽神秘的女孩,我不知道自己是否爱她,也许我只是在自暴自弃,但她为什么要随我到此,难道只是因为好奇。我放弃了思考,任音乐在脑中回响,桃花的香气如影随形,她说这叫做诱惑。
跳了一个小时的舞以后桃花说她要走了。其实还很早,不到十二点。我说要送她,她说不用了。我陪她走到门口,从口袋里掏出一张名片递给她。
你的名字很婉约嘛。她看过后笑道。
这是我的遗憾。我绷着脸回答,然后忍不住也笑。
她走的时候说再见。我没有回答,我讨厌说再见。
接下去一个月我忙得人仰马翻。彻夜不眠地在公司里对着电脑写程序,写得双眼无神皮肤枯槁,自己照镜子的时候都厌恶不已,我也不知道为什么要这样卖命,反正老板也不会给我加班津贴。忙起来会人的大脑总是转速飞快,一不留神就闪过和萱在一起的片断。还有桃花。她说过再见。这个城市很大也很小,如果你真想找一个人不会找不到。我知道自己可以在新天地看到她,但我不想去。我渴望着在阳光下和她重逢,我还没见过她不化妆的脸。阳光下的生活才是真实的,尽管也许可能很乏味。
在一个下午我接到了她的电话。当时我正在上班,手机上闪动陌生的号码,接起来后,传来略微沙哑的女声。
我是桃花。她说,我在你公司楼下。
哦,你等一下。我条件反射地说完,挂下电话就往楼下跑。电梯慢得让人心焦,仿佛足足过了一个世纪。
公司楼下是这个城市最繁华的地段,虽然不是休息日,人潮依然汹涌。她站在屈臣氏门口的台阶上,怀里抱着什么。
我走近去,才看清那是只小猫,只有手掌大小,白色的毛,粉红色的耳朵和脚掌。在她怀里茸茸地动。
我在住的地方附近捡到它的。她说,但是我不能带它回去。你能收养它吗。
我看了她半天,点了点头。我又能说什么呢。她素着一张脸,清纯得像个大学女生,又抱着这么个人见人爱的小东西。再说我原本也不讨厌猫。
那天下午我溜班和桃花送小猫回到了我的家。我们跪在地板上,看着那个小东西把用温水泡软的一小碟幼猫猫粮吃得干干净净,然后开始认真地舔自己的爪子。我和桃花都忍不住开始傻笑,笑了半天才发现腿都跪麻了。
拉她起来的时候,她的衣袖滑动,露出清晰可辨的细小针眼。虽然是夏天她却穿着长袖,原来是为了遮盖痕迹。
她微笑,并没有窘迫的神色。那显然是旧伤痕了。我没多说什么。
我们后来给小猫取名为点点。因为它的额头上有一小撮浅灰的毛。走的时候桃花抱着点点亲了又亲,我笑道,它还没洗澡呢,脏。
她听到这句话,突然微微楞了一下,她凝视我片刻,缓缓地说,要说脏,我才是最脏的。
我看着她在白天不那么妖娆却清澈如水的眼睛。我没多想,凑过去吻她,轻微的。她颤抖了一下,没有拒绝。
你是干净的。我说。下次来看点点。
桃花没有再来过,新天地也同样不见她的踪影。她突然就这样从我的生命中消失了,留下一只猫作为她曾经存在过的证明。
家里多了一只猫,不知怎的就突然多了几分生气。点点是只很有性格的猫,自从我给它分享了一次我做的红烧鸡翅,它就拒绝食用猫粮。无奈,只好我吃什么它吃什么,此猫酷爱鸡肉,咖喱的清炖的白斩的辣椒的来者拒,而且明显地对鱼没有兴趣。每天下班回家一开门就会看到它通常是睡眼朦胧地走到门口迎接我的样子,长久以来占据我心中的那片空白,突然就消失无踪了。
夜晚的新天地仍然是衣香鬓影,一个人的消失并不会造成任何不同。但是对我来说已经不同。遇见桃花以前我来这里只是为了杀时间,但现在却是为了等待某个人的出现。等待中时间会变得漫长,酒和香烟也不能排遣我的焦躁。所以,三个星期以后,我放弃了在新天地寻觅桃花的可能性。我问过自己,为什么没有问过她的联系方式,是我自己给了她随时离开的可能性,这其实也只是出于某种不确信。
我知道她有我的电话,手机以及家里的号码,上一次带点点回家的路上我问过她。她说之前问过明子,明子这个损友,无声无息地就把我卖了。
明子邀过我去老克的酒吧,我应景地去,但只觉得乏味。酒吧里经过我身旁的认识或不认识的女子,人人都眼波流转,其中没有一人有桃花那样的眼神。她的美在于其中隐含的脆弱,就像某种炫目却易碎的宝石。
去酒吧时总能看到萱,我现在已经能够不动声色地和她问好,有一次她跑过来扶在我的肩上和别人谈笑,不顾她的男友隐约露出不耐的神色。萱的爱好之一就是制造暧昧,对此我早已不会感觉无奈,不知道这算不算是一种境界。
那天我加班,到酒吧时差不多十点。明子在吧台另一端和一位年长的女性说话,我于是在宝儿身边坐下,宝儿就是明子的女友。
那个人是谁?我问宝儿。
不知道。明子说好像可以和她合作做些出口的生意。宝儿说。她的面前是一杯咖啡。这个酒吧里唯一一个雷打不动喝咖啡的人。宝儿是我所见过最优雅的女孩,如果不是因为她和明子从小青梅竹马,我想她一定不会坐在这个地方。
我们默默地坐了一会儿。其间我喝了半瓶喜力,抽了两支烟,和几个认识的人打了招呼。萱远远地在一个角落里冲我笑了一下。
你是不是很想念她?宝儿突如其来地开口问我。
没有。有些东西过去就过去了。我说。
我不是指萱。宝儿微笑,她有日本女孩子那样的单眼皮,素净的脸,你不会相信她是二十九岁。
我说的是上次你带来的那个穿黑衣服的女孩子。她接着说。
我微微一怔,没有回答。因为无论肯定还是否定都无从说出口。
恰好明子在这时回来,于是我们没有再继续这个话题。
明子笑着说,我可能要开始做宠物玩具了,到时候送你家猫猫一些。
我立即开心地回答,那就先谢过了。
没想到你是个爱猫的人呢,明子笑道,不过自从你养了点点,好像整个人都变得开朗了。
这么说我以前很阴郁了?
有点。宝儿答道。
我想我是个阴郁的人,从小到大。当你发现自己莫名其妙地喜欢压抑自己的喜好,当然会难免有些阴郁。何况我一向不擅长表达自己的想法,太多的感受都只会堆积在心里。毕业后我离开读书的北方城市,也没有回到乡,在这个完全陌生的城市里找了一份工作。也许我潜意识里是想要逃离过去与自己有关的一切,但人最后无法逃开的还是自己。我尝试换个活法,后来却发现那只是另一种形式的残忍。在这个城市里呆得愈久,愈觉得自己只是没有根的漂泊者。直到我遇见萱。
我还记得第二次遇见萱是在一个冬天的周日早上。那天的天空是这个城市少有的纯净的蓝。我的一个朋友打电话给我,说路过我住的地方。我于是叫她上来喝咖啡。她在电话里并没有说她不是一个人,开门后我看见了她身后的萱,雪白的围巾衬出因寒冷而绯红的双颊。
她的眼里满是明亮的笑意,她说,我们昨晚在酒吧见过呢。我的名字是萱,这个字的意思是忘忧草。
萱的职业是设计游戏软体,我们因此算得上是IT同行。她走的时候借了我的几本书。
那是单纯的开始,从借书还书开始,整个冬天里我们时常见面。一起看电影喝咖啡逛书店泡酒吧,后来更多的是在我家,我给她做菜,她在我的电脑上画些怪趣的图案。我问她和那天带她来的人是否很熟,她说那只是一个刚认识的朋友。等我发现自己陷入了毫不知情的三角恋情,已经是一种无法自拔的状态。
萱最后选择了我。我一直相信这是一种幸福。直至今天我也依然这么认为。尽管已经不再,但她在我身边的一年毕竟曾经真实地存在过。她只是无法不继续新的尝试,我可爱又可恨的忘忧草,她的天性就是做爱情的冒险。
似乎是一种讽刺,萱离开的时候是个雨天,我帮她把最后一箱行李搬上小型货车,然后她在雨里拥抱了我一下。
你恨我吗。她在我耳边说。
不。祝你幸福。我说。目送车子开远,我沉重地叹息,脸上冰凉的一定是雨水,我想。
我现在养成了听音乐台的习惯。音乐台的每个节目我都听,上班时也戴着耳机写代码,反正老板一向不管我们设计部门。音乐台的DJ都有好听的声音,拥有一个好听的声音真是一件很不错的事情,别人听着就会觉得心情愉快。特别喜欢一个女子的声音,她的名字叫做太平,主持晚上九点档的目。她选择的音乐都不是最IN的,但通常都具有自己的风格。太平有着略微沙哑的嗓音,低而柔和,在夜色渐深中轻轻扣击我的耳膜。通常都会在听她的节目时放弃做别的事,只是坐在沙发里,有时看着一本书,点点会在这时爬到我的膝盖上睡觉,咕噜着进入梦乡。
桃花打来电话的时候我正在听太平讲一个故事。
故事是这样的——
有一个喜欢写东西的女孩,她在BBS上遇到一个很投缘的人。两个人对于文学,音乐和很多东西都有相同的见解。女孩和那个人在网上聊了大半个月,终于忍不住提出见一面。
那个人说,你见到我会失望的。
女孩说,可我真的很想见到现实中的你。
于是他们就约定在某个咖啡馆见面,见面的时间是在黄昏。那个人说,我会穿黑色的衣服。
女孩在约定的时间到达了约定的地点。她在咖啡馆一角的位置坐了很久,以为自己终于没有等到那个人。就在她准备回去的时候,咖啡馆的男招待走过来对她说了一句话。
男招待说,对不起,我最后还是想告诉你,我并没有失约。
他穿的是黑色的T恤,黑色长裤。
太平的故事刚讲到这里,电话就急促地响了起来。点点在我的膝上睡成一个毛球,我只好尽可能轻地把它放在一边,然后拿起话筒。始料未及地听到桃花的声音,突然发现她的声线和太平极其相似,低而悦耳。
好吗。她说。
勉强活着。我答道。太平没有继续讲她的故事,开始放一首皇后乐队的曲子。
现在有空吗?
嗯。你在哪里?
我在公用电话亭。
嗯?
我没带手机。她轻笑一下。故意没带,这样别人就找不到我了。所以只 好在电话亭给你打电话。
你在哪里的电话亭?
她报了一个路名。那是在以前曾经昌盛的酒吧区,据说现在那边已经寥落了。我在脑海中搜寻着对那附近的印象。
从你现在的位置到MAC远吗?我问她。那是我唯一有印象的一家酒吧的名字。
不远。她低声说。
到MAC等我好吗。我马上过去。
我用了二十分钟赶到MAC。出租车上我让司机放音乐台,没有听到太平继续讲那个故事。大概就在我换衣服出门搭车的这段时间里,她说完了这个故事,而结局不得而知。
那一带确实变得冷清,有家酒吧改成了火锅城,剩下的几家也一副惨淡景象,当然,这和今天是星期四不无关系。桃花坐在MAC的吧台边,我一进门就看到了她。她穿的不是黑色,而是桃红色。这是险恶的颜色,稍有不慎就恶俗不堪。桃红色九分袖修身长裙,透明镶水钻高跟凉鞋,她的侧影如果不是置身于这个只有酒保在寂寥地擦杯子的地方,一定能勾住每一个人的目光。
我走进去,要了一杯杰克丹尼加可乐,然后我和她起身到二楼,这家酒吧的二楼有着老式的巨大玻璃窗,我们坐在窗下的沙发座里,我开了窗,窗外有香樟树,空气里是夏末夜晚特有的气息。
我又一次闻到了她身上的香气,若有若无地,不是上次的“诱惑”,而是我喜爱熟悉的KENZO的“泉”。
她几乎总是能猜到我在想什么。这是你的味道,她低笑道。我很喜欢,于是买来用。
你的裙子很漂亮。我只好说。
我刚从一个酒会上逃出来,因为这个。她说着,从银色的CK手袋里拿出一个丝绒盒子递给我。
我打开来看,其实不用看我也知道那是什么。盒子上有Tiffany的标记。
看到那个钻戒的时候我忍不住想,虽然钻石不能代表什么,但是如果一个男人肯送这样的钻戒给女子求婚,那不能说是不真诚的了。我的脑中闪过“从良”这个词,立刻又觉得自己的想法太过猥琐。
桃花目不转睛地注视着我,并且微笑,古怪精灵的女子,我永远无法预知她下一步会说什么做什么。
送我这个东西的人,是你们所谓的高级公务员。她开口道。
你没有同意也没有拒绝,是么。
要说我不动心,是假的。我也向往安定的生活。她点了一支烟,我记得她以前不是抽七星的,但又觉得她现在换成这个牌子不会是因为我的缘故。自从她出现,我就开始神神经经的,一点也不象我自己。
但是我不能。她笑一下,眼睛里殊无笑意。一直以来,我是某个人的专属物,她说,尽管这不是出于我的本意,所以我其实并没有选择自己生活的自由。
我喝了一口酒。可乐的甜味调和了威士忌的苦涩,有时候你会忘记它其实是一种酒。这个世界上充满了甜美的假象。
你一直没来看点点。我说,是出于同样的理由吧?
什么样的人能够拥有桃花这样的女子,在回家的路上,我忍不住设想。有钱,或者有权,更有可能是两者皆有。而我不过是这个城市里一个无足轻重的小人物,在西区写字楼叠立的街道上象我这样的人随手可找到一打,更何况我甚至不能够递给她一枚戒指光明正大地求婚,那枚戒指上也不会有优雅的多面体结晶。
但桃花所渴求的显然并不只是这些,因此她才对我另眼相看。过了一定的年龄,人与人的交往就会渐渐变得功利,所求不外乎名利身体或感情。我不知道自己能带给她什么,或许只是某种新鲜感,但即便如此也没有关系,我对自己说。
我只是想要见到她,再见到她,仅此而已。
周五的晚上公司有个酒会,算是庆祝我们的小组完成了一个大型的Job。我不太想出席,但没有合适的理由,只好随着大队人马杀到一家位于大厦九楼的据说相当有名的四川餐厅。餐厅内部装潢算得上金碧辉煌,大堂中央有个女孩子弹着钢琴伴奏,我们一行十八个人挤进一间摆着两张八仙桌的爆房。老板发表饭前演说的时候我一直盯着茶杯发呆,心想在这里听不见钢琴的声音真是可惜。菜上齐以后大家兴高采烈地开吃,不算太地道的川味,辣椒总嫌不够强劲。公司里大多是三十不到的年轻男孩子,一时间我周围酒杯碰撞声不绝于耳。我低头只顾自己吃菜,有人敬酒时就用可乐相待。想想心里有点悲哀,这么多年来我都小心地把自己隐藏得很好。我在同事们面前不抽烟不喝酒不谈私人问题,没有人知道我身边的女孩来了又去。
饭吃得差不多的时候我走开去洗手间,一打开包房的门就听得外面一阵喧闹。弹琴的女孩子仍在弹奏不止,但在这么嘈杂的环境里恐怕没有人听得清她的演奏。我走过一排包房的门口,洗手间在走廊的另一头,端着菜的服务生从我身旁擦肩而过。
洗手间里有人,我站在门口,燃起一支烟,隔壁门开了。我无意转过去看见那个人的脸,于是呆住。
是萱。
她穿着白色无袖长裙,长发在脑后挽成一个髻,衬出精巧的耳廓上闪亮的珍珠耳钉。我从未看过萱这么正式的样子。我想起以前在某本杂志上看到的话,说在人口超过一千万的城市偶遇分手恋人的比率约等于走在人行道上时被车撞到的机率。这句话显然是胡说八道。当然我在老克的酒吧里也常常遇见她,但在那之外的场合相遇这还是第一次。
萱站在原地看了我一秒,眼睛里飞快地闪过复杂的表情。
我的一个设计拿了奖,我们公司今天在这里吃饭。她先开口说。
哦,我也是公司吃饭。
结束后……你有安排吗?
没有。我说。总不能告诉她我在等一个可能不会出现的电话,为了一个认识一个月的女子。
我想要你陪我去酒吧。好吗?萱习惯在命令句式后面加一个确认,但那不过是形式。
我们不用站在洗手间门口谈话吧。我淡淡地说,待会儿你散场后给我发个短信。
她说夜是她的颜色。
遇见她是在新天地某个酒吧的露天座,夏天的夜晚,我百无聊赖地耗掉一包七星,正在喝第三杯不加冰块的龙舌兰酒,这玩意儿干喝味道简直同酒精无异。十点刚过,整个新天地的人气已经开始疯长,到处满座,老外们拿着杯子在座位间穿梭,露天座旁也三三两两站着闲谈或等待的人。
我在心里暗自决定,要是第三次看到那个女孩经过,我就请她喝一杯。
这么想不仅是因为她很美。你很容易在新天地遇见美女,其概率远远超过在这个城市的任何一个角落。别问我这是为什么,你只要来这里坐过就知道了,当你闻到这里混合着烟味、香水味、酒精味以及人们的各种莫名欲望和无聊感的气味后,你就知道为什么我喜欢坐在新天地的露天座观赏各色行人了。
尽管看了这么多人,但这个在十分钟之内两次经过我眼前的女孩子,总有某种让人牵动的地方。
她当然是穿着黑色,就像很多女孩子一样,在这样明亮的夜色里,用比夜更深的颜色来隐藏自己。我注意到她,是因为她明媚夺人的眼神,还有,她两次闯入我的视线时,都携着不同的女子。那两个妆容精致的女子在她的映照下,不能不显出花容失色的秋香式对比。
有那么多的人从我眼前经过,我几乎快要失去耐心了。这就像是一个狩猎游戏,只不过被猎者毫不知情。
她再次出现在我面前时,我刚刚喝完杯底的酒。时间正好够我走到她面前,我尽量从容不迫地问道,能不能请她喝杯酒。
没有迟疑,她笑了,并且点头。笑容一如我想象般甜美。
在这么短短几秒钟里,我的座位已经被人占领了。我只好和她走进嘈杂的室内。
我们找了个墙角的高脚桌放上酒杯,没有位子,只能站着。这个位置能看到歌手的侧脸,满室冰蓝色的灯光,她的脸就在这样的光线里凄迷地美艳着。
我们喝酒,只是喝酒,没有交谈。她很快地喝完了杯子里的伏特加和橙汁的混合物,冲我嫣然一笑。
谢谢你的酒,她说。不过很可惜我要回去工作了。她的声音沙哑,没有一丝做作的意味。
你在这里工作?
对。
那你什么时候下班?
我不知道。可能会很晚。
没关系,那我等你。
她用一只手把头发向后掠了一下,看了我一眼。然后她说,知道吗,这些话我听得多了,不过我还是第一次听到这样的话从一个孩子的嘴里说出来。
说完这些话,她就走了。留下我一个人看着蓝色灯光下模糊的人群。我开始等,因为我想告诉她我不是个孩子,我觉得自己已经老了。而且她没说不让我等。
她也没说她会回来。
那天她回来的时候是午夜两点。有的酒吧打烊了,有的还没有。人群逐渐退却。我的胃有灼烧的感觉,因为我不负责任地灌了那么多酒的缘故。忘记是哪个朋友说的了,过了二十五岁就应该学会爱惜自己,可惜我并不是常常能够做到。
我所在的酒吧开始清场,围着黑围裙的water跑过来问我是否还要点酒。我摇摇头,正准备走,肩上突然感觉到轻柔的压力。一转头,正看见她的笑容。也许是因为酒精的作用,我竟然有些许的恍惚,以为这不过是自己的幻觉。直到她开始说话。
你没走。她说。
我说过要等你的。
如果我不回来呢。
那我明天还会再来。
这样做有什么意义呢。
至少可以看见你。我笑笑,说,我没别的意思,只是想看看你。
她注视了我一秒钟,然后说,这里的人都叫我桃花。
我说,别人都叫我飞鸟。
那天后来我们去了新天地附近的一个绿地里聊天。那个绿地有一个人造湖,晚上沿着湖开了一溜灯,湖边几乎无人,很安静。她从酒吧买了一瓶杰克丹尼,又拿了两个杯子——她好像和这里的酒保很熟——我们就坐在湖边的台阶上喝酒聊天,那天我也许喝了这辈子最多的酒,后来我醉了,很可能吐过,但第二天起来的时候脑子几乎一片空白。
我只依稀记得我和她讲了阮宁的事。阮宁是我在大学时代的女友,大学毕业后我们就各奔东西不再联系,彼此似乎是刻意地维持着生疏的距离,装作什么也不记得。人有时候就是这么自欺欺人。我曾经那么地爱她,在每一个寒冷的早晨为她从食堂买好热气腾腾的早饭,秋天里我们骑自行车去郊外,我拍了那么多她的相片,在铺满红叶的小径。所有的亲吻和誓言,所有的肌肤温暖,终于在现实的空气中变淡,淡得像一张写满字却在洗衣机里被揉成一团的情书,连落款和抬头都辨认不清。
我不知道为什么要和这个刚刚认识的漂亮女孩子说这些。我连她姓什么都不知道。我只知道她叫桃花,该死的网络时代,每个人都习惯了用若干个ID,每一张面具的背后,其实都是无聊疲倦的面孔。我一边想着这些,一边絮絮叨叨地和她说阮宁,其实只是因为我醉了。
我记得自己上一次喝醉是什么时候,那是在大学毕业前的同学聚会上。我不是轻易会让自己陷入失控状态的人。太冷静,有时只是一种悲哀。
我从酒醉中醒过来后的第一件事,就是看现在几点钟。下午两点。看完后才想起来今天是星期六,不用上班,于是决定继续睡。但见鬼的是我清醒无比,甚至没有宿醉后应有的头痛,失去了自暴自弃的资格,我只好爬起来打扫房间。
这时才看到桌上有张纸。上面写着,钥匙在你的包里,我擅自取了开门,已经放回去了。地址是你自己和出租车司机说的。豆浆油条是我买的。不用道谢。
字写得很有力,间距很开,是出自利落性格的人之手。
我又重新看了一遍那张字条,然后开始坐在桌前吃豆浆油条。豆浆已经冷了,油条也已经发软,但对于饥肠辘辘的我来说是无上的美味。很久没有吃这些东西的习惯了,早餐我通常都是牛奶加几片饼干对付过去就算。想到那个一袭黑衣的名叫桃花的女孩子排在清晨买菜归来的阿姨爷叔中买早饭的场景,我不禁微笑。
五点多的时候接到明子打来的一个电话。他说,今天晚上有聚会,问我去不去。
我有事。我对他说,不去了。再说去了也没什么意思。
是不是因为有不想看到的人。他在电话的那一头轻笑道。
我可没有什么不想看到的人。我对着话筒说,我才没那么无聊。不玩这种新伤旧恨的把戏。我是真的有事。
那就算了。他说,你可不要硬撑哦,实在受不了可以到我这里来哭泣嘛。我的肩膀也可以偶尔借你一用的。
我笑起来。他不会知道,我已经畅快淋漓地哭过了,在一个陌生女子的肩头。依稀记起她的香水,陌生的绮艳的味道。
挂上明子的电话,我看着窗外发了一会儿呆。分手是一件很平常的事,无非是各奔东西罢了,最初的时候会有些不适,但说真的有什么不会成为过去呢。我知道自己不是因为怕看见萱而不敢出现,我只是觉得疲倦,就像野兽厌倦了它的角逐。她曾经说过将爱我至永远,她们都这样重复着同样的话语,最终却都离我而去。只留下回忆,就像债务一样让人喘不过气。
但至少生活中还有值得期待的事,我知道晚上我可以在新天地看见桃花。
她今天穿的仍是黑色。不同的黑,质地和款式造就了她的千变万化。如果说昨晚她的美艳吸引了我,那么今晚她的温婉则更加动人。
头痛吗。她款款走到我跟前问我。我坐在昨天相识的酒吧吧台一角,像个好孩子一样喝着一杯不含酒精的干姜水。
状态好极了。我说。谢谢你昨天送我回家。
我不是说过不用道谢了吗,她淡然道。她拿出烟,我顺手帮她点上。她低头对烟的时候,睫毛像蝴蝶的翅膀一样轻颤,让人有亲吻的欲望。她真是美。我注视她,心里在想,这样的女孩子,一定早已被某个人拥有。但这也没什么值得羡慕的,女孩子让人头痛的程度往往与其美丽程度成正比。
你今天不用去上班吗。她在我身旁坐了足足有一刻钟后,我问她。
我今天休息。她转动着手里的红酒杯子看杯壁流转的血红颜色,说。
周六休息岂不是太可惜了,周六生意会比较好。
你怎么知道我做的是什么生意,你又怎么知道周六生意好不好。她笑起来。
我知道的。我看着她的眼睛说,你做的是人的生意。
你真聪明,她喝了一口酒,说,你不如直白地说更恰当些,我确实是个卖家。而且我不仅卖自己,也卖别人。
我的脑海中顿时闪出三个字,但我不想把这么伧俗的字眼和她对号入座。于是我只是喝了一大口干姜水,彻底的冰凉使得喉咙一阵麻木。
你现在想做什么,她问,我今天有空,陪你散心。
我不需要散心。我说,不过谢谢你陪我。你想不想跳舞?
在这里?
我转头四顾,周围的人群几乎让人分辨不出自己所在的国度,我看了看高大傲慢肥胖的白种男人和他们身边笑容暧昧的黑发女人,对她说,不在这里,我领你去一个地方。
当我和桃花一同走进那家酒吧的时候,我知道自己多少带有报复的意味。她也确实达到了我所预期的效果,四下投射过来的目光,带有各种不同的含义。我走到明子旁边的位子让她坐下,明子和她的女友同时复杂地看了我一眼。然后明子对酒吧的主人老克说,给飞鸟来瓶百威。
桃花说,我要一杯红粉佳人,不要加蛋清。自从走进这里,她的神色没有丝毫变化,仿佛一切都顺理成章。
老克也对她露出一点惊艳的表情,或许只是出于虚伪。这不重要。每个来这里的人都有着自己黑暗的一面,重要的是我们可以在这里找到安慰和认同。
老克把酒端上来的间隙,明子低声问我,在哪里认识她的。
新天地,我说。
那么她是不是……?明子略带惊讶地说。
我不知道。这不重要吧。我说。我们只是来跳舞的。
我们只是来跳舞的。因为在这里跳舞不会有别人特殊的眼光来打扰。我拉着桃花的手走入中间的舞池,音乐强劲地包围着我,我开始在音乐中摆动身体,她的面容在镭射光束的闪烁中忽隐忽现。
不知何时,音乐变成了蓝调。我想都没想就环住了她的腰。很柔软。她的幽香划过我的脸。
你用的是什么香水。我低声在她耳旁问。
这支香水的名字叫作诱惑。她说,你以前的女朋友今天来了吗。
你指哪一个?我问。
最近分手的那一个。
我不记得自己是否告诉过她有关萱的事情,不过这已经不重要了。
她在角落里,我说,穿白衣的那个。
我拥着她慢慢旋转,以使她看到萱。萱并没有看我。她在和身旁的一个女孩子笑着交谈,也许她一开始就没看到我,也许她看到了却装作没看到,又或许她看到了但是无所谓。我还记得第一次在这里邂逅她的情景,那时她也是穿白衣,她的眼睛在夜色里明亮又温暖。我也记得在某个清晨,她坐在床头递给我一碗热粥。三百多个日夜。一年。然而一切说变就变。她走的时候没有解释这是为什么。我也不想听到任何所谓的解释。
我想我并不是没有留恋,但我已经学会将一切看得很淡,就像此刻,我看到夜色里的萱,心里只有一片空虚的茫然。也许是因为已经忘记了如何疼痛。爱一个人很容易,忘却也很容易。我的面前是个美丽神秘的女孩,我不知道自己是否爱她,也许我只是在自暴自弃,但她为什么要随我到此,难道只是因为好奇。我放弃了思考,任音乐在脑中回响,桃花的香气如影随形,她说这叫做诱惑。
跳了一个小时的舞以后桃花说她要走了。其实还很早,不到十二点。我说要送她,她说不用了。我陪她走到门口,从口袋里掏出一张名片递给她。
你的名字很婉约嘛。她看过后笑道。
这是我的遗憾。我绷着脸回答,然后忍不住也笑。
她走的时候说再见。我没有回答,我讨厌说再见。
接下去一个月我忙得人仰马翻。彻夜不眠地在公司里对着电脑写程序,写得双眼无神皮肤枯槁,自己照镜子的时候都厌恶不已,我也不知道为什么要这样卖命,反正老板也不会给我加班津贴。忙起来会人的大脑总是转速飞快,一不留神就闪过和萱在一起的片断。还有桃花。她说过再见。这个城市很大也很小,如果你真想找一个人不会找不到。我知道自己可以在新天地看到她,但我不想去。我渴望着在阳光下和她重逢,我还没见过她不化妆的脸。阳光下的生活才是真实的,尽管也许可能很乏味。
在一个下午我接到了她的电话。当时我正在上班,手机上闪动陌生的号码,接起来后,传来略微沙哑的女声。
我是桃花。她说,我在你公司楼下。
哦,你等一下。我条件反射地说完,挂下电话就往楼下跑。电梯慢得让人心焦,仿佛足足过了一个世纪。
公司楼下是这个城市最繁华的地段,虽然不是休息日,人潮依然汹涌。她站在屈臣氏门口的台阶上,怀里抱着什么。
我走近去,才看清那是只小猫,只有手掌大小,白色的毛,粉红色的耳朵和脚掌。在她怀里茸茸地动。
我在住的地方附近捡到它的。她说,但是我不能带它回去。你能收养它吗。
我看了她半天,点了点头。我又能说什么呢。她素着一张脸,清纯得像个大学女生,又抱着这么个人见人爱的小东西。再说我原本也不讨厌猫。
那天下午我溜班和桃花送小猫回到了我的家。我们跪在地板上,看着那个小东西把用温水泡软的一小碟幼猫猫粮吃得干干净净,然后开始认真地舔自己的爪子。我和桃花都忍不住开始傻笑,笑了半天才发现腿都跪麻了。
拉她起来的时候,她的衣袖滑动,露出清晰可辨的细小针眼。虽然是夏天她却穿着长袖,原来是为了遮盖痕迹。
她微笑,并没有窘迫的神色。那显然是旧伤痕了。我没多说什么。
我们后来给小猫取名为点点。因为它的额头上有一小撮浅灰的毛。走的时候桃花抱着点点亲了又亲,我笑道,它还没洗澡呢,脏。
她听到这句话,突然微微楞了一下,她凝视我片刻,缓缓地说,要说脏,我才是最脏的。
我看着她在白天不那么妖娆却清澈如水的眼睛。我没多想,凑过去吻她,轻微的。她颤抖了一下,没有拒绝。
你是干净的。我说。下次来看点点。
桃花没有再来过,新天地也同样不见她的踪影。她突然就这样从我的生命中消失了,留下一只猫作为她曾经存在过的证明。
家里多了一只猫,不知怎的就突然多了几分生气。点点是只很有性格的猫,自从我给它分享了一次我做的红烧鸡翅,它就拒绝食用猫粮。无奈,只好我吃什么它吃什么,此猫酷爱鸡肉,咖喱的清炖的白斩的辣椒的来者拒,而且明显地对鱼没有兴趣。每天下班回家一开门就会看到它通常是睡眼朦胧地走到门口迎接我的样子,长久以来占据我心中的那片空白,突然就消失无踪了。
夜晚的新天地仍然是衣香鬓影,一个人的消失并不会造成任何不同。但是对我来说已经不同。遇见桃花以前我来这里只是为了杀时间,但现在却是为了等待某个人的出现。等待中时间会变得漫长,酒和香烟也不能排遣我的焦躁。所以,三个星期以后,我放弃了在新天地寻觅桃花的可能性。我问过自己,为什么没有问过她的联系方式,是我自己给了她随时离开的可能性,这其实也只是出于某种不确信。
我知道她有我的电话,手机以及家里的号码,上一次带点点回家的路上我问过她。她说之前问过明子,明子这个损友,无声无息地就把我卖了。
明子邀过我去老克的酒吧,我应景地去,但只觉得乏味。酒吧里经过我身旁的认识或不认识的女子,人人都眼波流转,其中没有一人有桃花那样的眼神。她的美在于其中隐含的脆弱,就像某种炫目却易碎的宝石。
去酒吧时总能看到萱,我现在已经能够不动声色地和她问好,有一次她跑过来扶在我的肩上和别人谈笑,不顾她的男友隐约露出不耐的神色。萱的爱好之一就是制造暧昧,对此我早已不会感觉无奈,不知道这算不算是一种境界。
那天我加班,到酒吧时差不多十点。明子在吧台另一端和一位年长的女性说话,我于是在宝儿身边坐下,宝儿就是明子的女友。
那个人是谁?我问宝儿。
不知道。明子说好像可以和她合作做些出口的生意。宝儿说。她的面前是一杯咖啡。这个酒吧里唯一一个雷打不动喝咖啡的人。宝儿是我所见过最优雅的女孩,如果不是因为她和明子从小青梅竹马,我想她一定不会坐在这个地方。
我们默默地坐了一会儿。其间我喝了半瓶喜力,抽了两支烟,和几个认识的人打了招呼。萱远远地在一个角落里冲我笑了一下。
你是不是很想念她?宝儿突如其来地开口问我。
没有。有些东西过去就过去了。我说。
我不是指萱。宝儿微笑,她有日本女孩子那样的单眼皮,素净的脸,你不会相信她是二十九岁。
我说的是上次你带来的那个穿黑衣服的女孩子。她接着说。
我微微一怔,没有回答。因为无论肯定还是否定都无从说出口。
恰好明子在这时回来,于是我们没有再继续这个话题。
明子笑着说,我可能要开始做宠物玩具了,到时候送你家猫猫一些。
我立即开心地回答,那就先谢过了。
没想到你是个爱猫的人呢,明子笑道,不过自从你养了点点,好像整个人都变得开朗了。
这么说我以前很阴郁了?
有点。宝儿答道。
我想我是个阴郁的人,从小到大。当你发现自己莫名其妙地喜欢压抑自己的喜好,当然会难免有些阴郁。何况我一向不擅长表达自己的想法,太多的感受都只会堆积在心里。毕业后我离开读书的北方城市,也没有回到乡,在这个完全陌生的城市里找了一份工作。也许我潜意识里是想要逃离过去与自己有关的一切,但人最后无法逃开的还是自己。我尝试换个活法,后来却发现那只是另一种形式的残忍。在这个城市里呆得愈久,愈觉得自己只是没有根的漂泊者。直到我遇见萱。
我还记得第二次遇见萱是在一个冬天的周日早上。那天的天空是这个城市少有的纯净的蓝。我的一个朋友打电话给我,说路过我住的地方。我于是叫她上来喝咖啡。她在电话里并没有说她不是一个人,开门后我看见了她身后的萱,雪白的围巾衬出因寒冷而绯红的双颊。
她的眼里满是明亮的笑意,她说,我们昨晚在酒吧见过呢。我的名字是萱,这个字的意思是忘忧草。
萱的职业是设计游戏软体,我们因此算得上是IT同行。她走的时候借了我的几本书。
那是单纯的开始,从借书还书开始,整个冬天里我们时常见面。一起看电影喝咖啡逛书店泡酒吧,后来更多的是在我家,我给她做菜,她在我的电脑上画些怪趣的图案。我问她和那天带她来的人是否很熟,她说那只是一个刚认识的朋友。等我发现自己陷入了毫不知情的三角恋情,已经是一种无法自拔的状态。
萱最后选择了我。我一直相信这是一种幸福。直至今天我也依然这么认为。尽管已经不再,但她在我身边的一年毕竟曾经真实地存在过。她只是无法不继续新的尝试,我可爱又可恨的忘忧草,她的天性就是做爱情的冒险。
似乎是一种讽刺,萱离开的时候是个雨天,我帮她把最后一箱行李搬上小型货车,然后她在雨里拥抱了我一下。
你恨我吗。她在我耳边说。
不。祝你幸福。我说。目送车子开远,我沉重地叹息,脸上冰凉的一定是雨水,我想。
我现在养成了听音乐台的习惯。音乐台的每个节目我都听,上班时也戴着耳机写代码,反正老板一向不管我们设计部门。音乐台的DJ都有好听的声音,拥有一个好听的声音真是一件很不错的事情,别人听着就会觉得心情愉快。特别喜欢一个女子的声音,她的名字叫做太平,主持晚上九点档的目。她选择的音乐都不是最IN的,但通常都具有自己的风格。太平有着略微沙哑的嗓音,低而柔和,在夜色渐深中轻轻扣击我的耳膜。通常都会在听她的节目时放弃做别的事,只是坐在沙发里,有时看着一本书,点点会在这时爬到我的膝盖上睡觉,咕噜着进入梦乡。
桃花打来电话的时候我正在听太平讲一个故事。
故事是这样的——
有一个喜欢写东西的女孩,她在BBS上遇到一个很投缘的人。两个人对于文学,音乐和很多东西都有相同的见解。女孩和那个人在网上聊了大半个月,终于忍不住提出见一面。
那个人说,你见到我会失望的。
女孩说,可我真的很想见到现实中的你。
于是他们就约定在某个咖啡馆见面,见面的时间是在黄昏。那个人说,我会穿黑色的衣服。
女孩在约定的时间到达了约定的地点。她在咖啡馆一角的位置坐了很久,以为自己终于没有等到那个人。就在她准备回去的时候,咖啡馆的男招待走过来对她说了一句话。
男招待说,对不起,我最后还是想告诉你,我并没有失约。
他穿的是黑色的T恤,黑色长裤。
太平的故事刚讲到这里,电话就急促地响了起来。点点在我的膝上睡成一个毛球,我只好尽可能轻地把它放在一边,然后拿起话筒。始料未及地听到桃花的声音,突然发现她的声线和太平极其相似,低而悦耳。
好吗。她说。
勉强活着。我答道。太平没有继续讲她的故事,开始放一首皇后乐队的曲子。
现在有空吗?
嗯。你在哪里?
我在公用电话亭。
嗯?
我没带手机。她轻笑一下。故意没带,这样别人就找不到我了。所以只 好在电话亭给你打电话。
你在哪里的电话亭?
她报了一个路名。那是在以前曾经昌盛的酒吧区,据说现在那边已经寥落了。我在脑海中搜寻着对那附近的印象。
从你现在的位置到MAC远吗?我问她。那是我唯一有印象的一家酒吧的名字。
不远。她低声说。
到MAC等我好吗。我马上过去。
我用了二十分钟赶到MAC。出租车上我让司机放音乐台,没有听到太平继续讲那个故事。大概就在我换衣服出门搭车的这段时间里,她说完了这个故事,而结局不得而知。
那一带确实变得冷清,有家酒吧改成了火锅城,剩下的几家也一副惨淡景象,当然,这和今天是星期四不无关系。桃花坐在MAC的吧台边,我一进门就看到了她。她穿的不是黑色,而是桃红色。这是险恶的颜色,稍有不慎就恶俗不堪。桃红色九分袖修身长裙,透明镶水钻高跟凉鞋,她的侧影如果不是置身于这个只有酒保在寂寥地擦杯子的地方,一定能勾住每一个人的目光。
我走进去,要了一杯杰克丹尼加可乐,然后我和她起身到二楼,这家酒吧的二楼有着老式的巨大玻璃窗,我们坐在窗下的沙发座里,我开了窗,窗外有香樟树,空气里是夏末夜晚特有的气息。
我又一次闻到了她身上的香气,若有若无地,不是上次的“诱惑”,而是我喜爱熟悉的KENZO的“泉”。
她几乎总是能猜到我在想什么。这是你的味道,她低笑道。我很喜欢,于是买来用。
你的裙子很漂亮。我只好说。
我刚从一个酒会上逃出来,因为这个。她说着,从银色的CK手袋里拿出一个丝绒盒子递给我。
我打开来看,其实不用看我也知道那是什么。盒子上有Tiffany的标记。
看到那个钻戒的时候我忍不住想,虽然钻石不能代表什么,但是如果一个男人肯送这样的钻戒给女子求婚,那不能说是不真诚的了。我的脑中闪过“从良”这个词,立刻又觉得自己的想法太过猥琐。
桃花目不转睛地注视着我,并且微笑,古怪精灵的女子,我永远无法预知她下一步会说什么做什么。
送我这个东西的人,是你们所谓的高级公务员。她开口道。
你没有同意也没有拒绝,是么。
要说我不动心,是假的。我也向往安定的生活。她点了一支烟,我记得她以前不是抽七星的,但又觉得她现在换成这个牌子不会是因为我的缘故。自从她出现,我就开始神神经经的,一点也不象我自己。
但是我不能。她笑一下,眼睛里殊无笑意。一直以来,我是某个人的专属物,她说,尽管这不是出于我的本意,所以我其实并没有选择自己生活的自由。
我喝了一口酒。可乐的甜味调和了威士忌的苦涩,有时候你会忘记它其实是一种酒。这个世界上充满了甜美的假象。
你一直没来看点点。我说,是出于同样的理由吧?
什么样的人能够拥有桃花这样的女子,在回家的路上,我忍不住设想。有钱,或者有权,更有可能是两者皆有。而我不过是这个城市里一个无足轻重的小人物,在西区写字楼叠立的街道上象我这样的人随手可找到一打,更何况我甚至不能够递给她一枚戒指光明正大地求婚,那枚戒指上也不会有优雅的多面体结晶。
但桃花所渴求的显然并不只是这些,因此她才对我另眼相看。过了一定的年龄,人与人的交往就会渐渐变得功利,所求不外乎名利身体或感情。我不知道自己能带给她什么,或许只是某种新鲜感,但即便如此也没有关系,我对自己说。
我只是想要见到她,再见到她,仅此而已。
周五的晚上公司有个酒会,算是庆祝我们的小组完成了一个大型的Job。我不太想出席,但没有合适的理由,只好随着大队人马杀到一家位于大厦九楼的据说相当有名的四川餐厅。餐厅内部装潢算得上金碧辉煌,大堂中央有个女孩子弹着钢琴伴奏,我们一行十八个人挤进一间摆着两张八仙桌的爆房。老板发表饭前演说的时候我一直盯着茶杯发呆,心想在这里听不见钢琴的声音真是可惜。菜上齐以后大家兴高采烈地开吃,不算太地道的川味,辣椒总嫌不够强劲。公司里大多是三十不到的年轻男孩子,一时间我周围酒杯碰撞声不绝于耳。我低头只顾自己吃菜,有人敬酒时就用可乐相待。想想心里有点悲哀,这么多年来我都小心地把自己隐藏得很好。我在同事们面前不抽烟不喝酒不谈私人问题,没有人知道我身边的女孩来了又去。
饭吃得差不多的时候我走开去洗手间,一打开包房的门就听得外面一阵喧闹。弹琴的女孩子仍在弹奏不止,但在这么嘈杂的环境里恐怕没有人听得清她的演奏。我走过一排包房的门口,洗手间在走廊的另一头,端着菜的服务生从我身旁擦肩而过。
洗手间里有人,我站在门口,燃起一支烟,隔壁门开了。我无意转过去看见那个人的脸,于是呆住。
是萱。
她穿着白色无袖长裙,长发在脑后挽成一个髻,衬出精巧的耳廓上闪亮的珍珠耳钉。我从未看过萱这么正式的样子。我想起以前在某本杂志上看到的话,说在人口超过一千万的城市偶遇分手恋人的比率约等于走在人行道上时被车撞到的机率。这句话显然是胡说八道。当然我在老克的酒吧里也常常遇见她,但在那之外的场合相遇这还是第一次。
萱站在原地看了我一秒,眼睛里飞快地闪过复杂的表情。
我的一个设计拿了奖,我们公司今天在这里吃饭。她先开口说。
哦,我也是公司吃饭。
结束后……你有安排吗?
没有。我说。总不能告诉她我在等一个可能不会出现的电话,为了一个认识一个月的女子。
我想要你陪我去酒吧。好吗?萱习惯在命令句式后面加一个确认,但那不过是形式。
我们不用站在洗手间门口谈话吧。我淡淡地说,待会儿你散场后给我发个短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