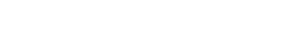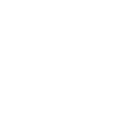豆腐块被子
大学里面对大一新生要求格外地严格,其严格程度3倍于大二学生,9倍于大三学生,81倍于大四学生,依此类推。如果研究事物的相似性,在这一点上,入学等同入狱。我来大学的第二天,我和人参还有sun就被导员找去,初以为趴窗户看女生让谁给举报了,结果证明不是。去过导办后才知道,是被叠得不合标准。叠被如做人,要叠到方正有度,刚正不阿。
大学里除了领导的心眼小外其他的都大。叠被也做出了学问,而且足够大,竟牵扯人格出来——不爱叠被的人,被叠得不好的人,人品也好不到哪去。叠被学就这样被做大做深,标准立得和本科学位一样高。
我们三个初来乍到对学校的布局设置还不清楚,两天来除了出外觅食没远走过,经多方咨询,曲折迂回总算找对了门。我们胆怯地敲了门,但凡犯了错误的人都心虚,尤其是不知道自己犯了什么错误,心更是忐忑地悬着。听见有人回应,我们推门进去,看见办公桌后面的椅子上坐着一个三十岁左右的男人,短头发,戴眼镜,看起来还算有文化,一小撮胡子徘徊在鼻子和上嘴唇间,典型的东洋人。现在名牌大学外教都多,干得好的,被纳如组织部也有可能。看他的操行大概就是个导员,不过看他的派头似乎是厅级以上的领导干部。
小胡子劈头盖脸就问:“你们为什么不叠被?”似乎一眼就能看出我们是不叠被一族。我们被问得哑口无言。本来被就是摊开睡的,怎么睡是我们自己的事,当然这种逻辑现在行不通。导员不是语重心长地说,也没和颜悦色,摆出老子训儿子的架势,那淫威就似急欲喷薄的火山,一吐为快。闻其言,如观其人。说的和长的差不多一样令人不悦,兴致尽扫。两者合在一起,感觉贴近进食过量的胃,饱胀欲呕。我们都没正眼看他,那张脸像是一粒随时可能糅入眼内的沙,让人避之心切。我们被告知每天都要叠被,而且被要叠得有棱有角,成豆腐块形状。我们寝室里四个人,有三个是刚刚来报到,没参加过军训,根本不知道豆腐块是怎么成型的,只知道被摊开了就是豆腐皮儿,不过导员说豆腐皮儿不行,非豆腐块不可。这样一来阿亮每天早上都要叠四床被。工作量这么大,时间长了阿亮肯定不干。没办法我们三个人为了应付检查,更不想再看到那张东洋脸。于是每人又各自买了一床被,阿亮用了一晚上时间帮我们把那三床被叠成标准的“豆腐块”,为了有鲜明的棱角和造型更为持久,我们把被层里嵌进薄木板。弄好了一动不动地供在那里,晚上从柜子里翻出另一床被来盖。
这样“供被”的日子持续了整整一年,大二来临之际,“豆腐皮儿”终于有了春天。
大学里面对大一新生要求格外地严格,其严格程度3倍于大二学生,9倍于大三学生,81倍于大四学生,依此类推。如果研究事物的相似性,在这一点上,入学等同入狱。我来大学的第二天,我和人参还有sun就被导员找去,初以为趴窗户看女生让谁给举报了,结果证明不是。去过导办后才知道,是被叠得不合标准。叠被如做人,要叠到方正有度,刚正不阿。
大学里除了领导的心眼小外其他的都大。叠被也做出了学问,而且足够大,竟牵扯人格出来——不爱叠被的人,被叠得不好的人,人品也好不到哪去。叠被学就这样被做大做深,标准立得和本科学位一样高。
我们三个初来乍到对学校的布局设置还不清楚,两天来除了出外觅食没远走过,经多方咨询,曲折迂回总算找对了门。我们胆怯地敲了门,但凡犯了错误的人都心虚,尤其是不知道自己犯了什么错误,心更是忐忑地悬着。听见有人回应,我们推门进去,看见办公桌后面的椅子上坐着一个三十岁左右的男人,短头发,戴眼镜,看起来还算有文化,一小撮胡子徘徊在鼻子和上嘴唇间,典型的东洋人。现在名牌大学外教都多,干得好的,被纳如组织部也有可能。看他的操行大概就是个导员,不过看他的派头似乎是厅级以上的领导干部。
小胡子劈头盖脸就问:“你们为什么不叠被?”似乎一眼就能看出我们是不叠被一族。我们被问得哑口无言。本来被就是摊开睡的,怎么睡是我们自己的事,当然这种逻辑现在行不通。导员不是语重心长地说,也没和颜悦色,摆出老子训儿子的架势,那淫威就似急欲喷薄的火山,一吐为快。闻其言,如观其人。说的和长的差不多一样令人不悦,兴致尽扫。两者合在一起,感觉贴近进食过量的胃,饱胀欲呕。我们都没正眼看他,那张脸像是一粒随时可能糅入眼内的沙,让人避之心切。我们被告知每天都要叠被,而且被要叠得有棱有角,成豆腐块形状。我们寝室里四个人,有三个是刚刚来报到,没参加过军训,根本不知道豆腐块是怎么成型的,只知道被摊开了就是豆腐皮儿,不过导员说豆腐皮儿不行,非豆腐块不可。这样一来阿亮每天早上都要叠四床被。工作量这么大,时间长了阿亮肯定不干。没办法我们三个人为了应付检查,更不想再看到那张东洋脸。于是每人又各自买了一床被,阿亮用了一晚上时间帮我们把那三床被叠成标准的“豆腐块”,为了有鲜明的棱角和造型更为持久,我们把被层里嵌进薄木板。弄好了一动不动地供在那里,晚上从柜子里翻出另一床被来盖。
这样“供被”的日子持续了整整一年,大二来临之际,“豆腐皮儿”终于有了春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