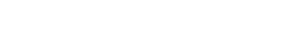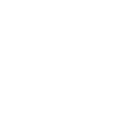“活着”:纸上,银幕上,尘世上
“以笑的方式哭,在死亡的伴随下活着。”
记得当年,我用两天时间一口气读完《许三观卖血记》后,马上到处去寻余华另一本代表作《活着》,然后一天半就看完了。
半年前,又从网上下载了张艺谋导演的《活着》。我觉得对余华, 对《活着》,该有一点发言权了。
我读《活着》时,几次忍不住哭出来,我承认,自己比较脆弱。
然而,脆弱也表明我的善良,虽说这话听着矫情。
自己有过苦难,因而同情他人的苦难,是一种善良:而自己没经历多少苦难,也能对他人的苦难抱有恻隐之心,则是另一种善良,更接近本真的善良,我以为。
小说改编为影视,自然会引发种种得与失、优与劣的评头论足。近些年,倒有不少原本默默无闻之作被搬上银幕后声名鹊起的,例如《鬼子来了》《盲井》(分别来自尤凤伟的《生存》和刘庆邦的《神木》)等:自然也有好端端的原著被编剧导演活活糟蹋掉的。纸上和银幕上同时大放异彩相得益彰的,委实不多,而《活着》算是典型一例,它成就了余华,也成就了张艺谋。
影片对小说的改编,我觉得最重要的在于叙事模式的转变,即由“宿命”到“体制”的转变。全片是笼罩在沉重而又喧闹,森严而又滑稽的“政治”气氛中的,高潮部分,即凤霞之死那场戏,原著只说因产后大出血而死在了用福贵的话说“与咱家有世仇”的医院里,而影片的安排却独具匠心:红卫兵小将夺了权,一群卫校生掌管着患者生死大权。而颇具戏剧性的一幕是,这边凤霞因大出血无法救治而在父母丈夫的凄惨哭喊中死去,一边却是真正优秀的医生,被打倒的反动学术权威王教授因三天没吃饭而一口气吃下七个馒头险些被撑死!强烈的对比度和细节的冲击力,使观众无不将愤怒更多撒向那个指鹿为马人妖颠倒人性集体沦丧的荒唐岁月!而这也正是早期张艺谋“反体制”的倾向所决定了的。这无疑加深了作品的批判深度。在此之前的细节铺垫中,政治运动中小人物的命运就一直是影片表达的重心,从龙二在“土改”中被枪毙,看见这一吓人场面的富贵尿了裤子,再到福贵那句“那不是我家的木头,那是反革命的木头!”从而庆幸幸亏当年做了败家子把家产输给龙二,以及凤夏出嫁时的“革命婚礼”上新郎官向伟大领袖毛主席请示他要接走他的媳妇,大跃进大炼钢铁时福贵的看家宝贝——那套皮影道具得以幸存但到了史无前例的文革还是最终难逃一劫,等等,都是具有鲜明的意识形态色彩的情境。有人批评老谋子的“史诗情结”,我要说,罗曼罗兰眼中唯一的英雄主义即“关注世界的真实面目并且爱世界”也是一种伟大的史诗情结,张导钟情于斯,这毕竟比如今的他所迷醉的“团体操情结”“魔幻情结”“大波妹情结”要高尚百倍。反观余华的小说呢?对政治背景的解毒完全依着主人公福贵个人的“角度”和“力度”,只说队长听上面的,我们听队长的,从他嘴里没听到更多的对社会现实的怀疑对体制力量的抵触,人们把命运的悲剧更多归咎于“命”而已,作者自述曰:“《活着.》讲述了一个人和他的命运之间的友情,这是最为感人的友情,他们互相感激,同时也互相仇恨。他们谁也无法抛弃对方,同时谁也没有理由抱怨对方。”这无疑体现了“人性的深度”,却不知不觉中淡化了故事的社会的,体制的背景。而电影所做,恰恰是对这种倾向的一个反动,余华还说:“《活着》讲述了眼泪的丰富与宽广,讲述了绝望的不存在,讲述了人是为了活着本身而活着。”看看,作者几乎是在刻意的回避一些什么。显然他主管上不想让人们对这部作品做过多政治化的解读。
总之,小说通过福贵的叙述多少带些超脱的感觉,而影片则明显带有一种入世的味道。
当然,如果仅从悲剧性角度审视,原作显然更胜一筹,小说当中,福贵所有的亲人都死掉了,他先后亲手埋葬了心爱的为了省鞋光脚跑步的儿子,懂事温顺却苦命加身的聋哑女儿,陪自己走过凄苦一生从来无一句怨言的妻子,在晚年,更致命的打击来临:先是女婿死在建筑工地,其后,活下去的在外人看来唯一的动力————小外孙意外死亡(太饿了,吃豆子撑死了),而他晚年的最好朋友和唯一贴心“人”,就是被他起了“福贵”名字的那头老牛。而电影只却表现了福贵一双儿女的离去,后面三个都特意掩去了,苦根还不叫苦根叫“馒头”,而且大概为了通过“审查”,干脆加上光明的媚俗的尾巴(可即便如此,当局至今年仍然不让这部片子见到天日),引起原作者的不满,也是情理之中的事。可以这么说,电影较之原著,“思想性”增强了,而“悲剧性”却削弱了。生存之道,使他不得不违心的歪曲乃至阉割原著里一些有分量的东西。
值得一提的是,影片对原著的改编,没有停留在机械的重复和照搬上,而是充分运用影像的特征创造充满活力的视觉语言,这也是作品的一大亮点,最有代表性的意象就是皮影。小说压根没提到这类东西,而电影中,它却几乎成了线索性的标志物,是福贵一生坎坷血泪的见证,尤其福贵扯开嗓子那几句唱,可谓愁肠百结神鬼皆惊。虚幻的皮影莫非是惨淡到无味悲凉到无泪的现实的反衬吧?人生如戏,戏梦人生,表面是人在操纵玩偶,实际上人又是块头更大的玩偶而已,极强又极稳妥的象征隐喻意味,使皮影成为改编中的神来之笔。这一点,也如同《菊豆》中大红大黄的染布条,《大红灯笼高高挂》中的红灯笼一样,是编导才气和胆识的体现。
电影中也有不如小说传神的细节,比如表现饥饿。不如小说触目惊心。我读到队长“主持公道”将刨出来的地瓜一分为三,甚至放弃队长的尊严来福贵家讨一小把米回去开饭的情节,心里那种酸楚,的确不是“煽情”的结果。
有批评家认为余华冷静过分,血管里流的不是血而是冰碴,余杰就曾批评它这位本家哥哥,只有肉体的“活着”而没有灵魂的求索,其实我觉得余杰未免言之过苛,把半个世纪以来中国底层民众的真实生存揭示给天下人,不为种种意识形态宣传所左右,以完全的冷静的写实展示苦难,唤起良知,在现今中国文坛,能做到及格水准,四海之大有几人欤?“形而上”的理性反思固然可贵,“形而下”的感性触动却是文学走进民众内心的第一步。
另外,不知电影改编者出于何种考虑,非要把福贵的儿子有庆的死安排为区长的车撞倒围墙砸死,而小说里是为救生孩子难产的县长夫人时硬给抽血抽死的!我看还是原著情节更具震撼力,底层民众的苦难,与权贵们的优越,就是一枚硬币的两面嘛。何况小说里最后写县长在文革中被逼自尽,也多少有种“报应”的影射在里面,在那个年代。谁敢保证自己会逃脱厄运的魔爪?海明威说得好:不要问丧钟为谁而鸣,它就为你敲响!没有基本法治与人权的保障,任何人都在侥幸活着而已。
我想起几年前,一位学生在她的随笔中问我:人活着究竟为了什么,我不假思索地回答:不要问人活着为什么,活着的目的就是活着。也许浸染于年少轻狂的学生并不恭维老师这一太缺乏诗意和“深度”的回答,不过,我相信总有一天她会懂的。
活着就是活着,活着好啊!哪怕只冲“你欠我们家一条命”(福贵夫妇对“误杀”自己儿子的春生如是说)这个理由,我们也得活下去!
对了,这部片子不仅是谋子的巅峰之作,也是演员葛优的最成功作品。他因此荣膺戛纳电影节最佳男主角。可惜因本篇禁映至今令好多人对此并不知情,以为葛优还是那个李东宝那个贺岁片里的“装蛋分子”最多是那个一旦生气后果就很严重的“黎叔”呢!
“以笑的方式哭,在死亡的伴随下活着。”
记得当年,我用两天时间一口气读完《许三观卖血记》后,马上到处去寻余华另一本代表作《活着》,然后一天半就看完了。
半年前,又从网上下载了张艺谋导演的《活着》。我觉得对余华, 对《活着》,该有一点发言权了。
我读《活着》时,几次忍不住哭出来,我承认,自己比较脆弱。
然而,脆弱也表明我的善良,虽说这话听着矫情。
自己有过苦难,因而同情他人的苦难,是一种善良:而自己没经历多少苦难,也能对他人的苦难抱有恻隐之心,则是另一种善良,更接近本真的善良,我以为。
小说改编为影视,自然会引发种种得与失、优与劣的评头论足。近些年,倒有不少原本默默无闻之作被搬上银幕后声名鹊起的,例如《鬼子来了》《盲井》(分别来自尤凤伟的《生存》和刘庆邦的《神木》)等:自然也有好端端的原著被编剧导演活活糟蹋掉的。纸上和银幕上同时大放异彩相得益彰的,委实不多,而《活着》算是典型一例,它成就了余华,也成就了张艺谋。
影片对小说的改编,我觉得最重要的在于叙事模式的转变,即由“宿命”到“体制”的转变。全片是笼罩在沉重而又喧闹,森严而又滑稽的“政治”气氛中的,高潮部分,即凤霞之死那场戏,原著只说因产后大出血而死在了用福贵的话说“与咱家有世仇”的医院里,而影片的安排却独具匠心:红卫兵小将夺了权,一群卫校生掌管着患者生死大权。而颇具戏剧性的一幕是,这边凤霞因大出血无法救治而在父母丈夫的凄惨哭喊中死去,一边却是真正优秀的医生,被打倒的反动学术权威王教授因三天没吃饭而一口气吃下七个馒头险些被撑死!强烈的对比度和细节的冲击力,使观众无不将愤怒更多撒向那个指鹿为马人妖颠倒人性集体沦丧的荒唐岁月!而这也正是早期张艺谋“反体制”的倾向所决定了的。这无疑加深了作品的批判深度。在此之前的细节铺垫中,政治运动中小人物的命运就一直是影片表达的重心,从龙二在“土改”中被枪毙,看见这一吓人场面的富贵尿了裤子,再到福贵那句“那不是我家的木头,那是反革命的木头!”从而庆幸幸亏当年做了败家子把家产输给龙二,以及凤夏出嫁时的“革命婚礼”上新郎官向伟大领袖毛主席请示他要接走他的媳妇,大跃进大炼钢铁时福贵的看家宝贝——那套皮影道具得以幸存但到了史无前例的文革还是最终难逃一劫,等等,都是具有鲜明的意识形态色彩的情境。有人批评老谋子的“史诗情结”,我要说,罗曼罗兰眼中唯一的英雄主义即“关注世界的真实面目并且爱世界”也是一种伟大的史诗情结,张导钟情于斯,这毕竟比如今的他所迷醉的“团体操情结”“魔幻情结”“大波妹情结”要高尚百倍。反观余华的小说呢?对政治背景的解毒完全依着主人公福贵个人的“角度”和“力度”,只说队长听上面的,我们听队长的,从他嘴里没听到更多的对社会现实的怀疑对体制力量的抵触,人们把命运的悲剧更多归咎于“命”而已,作者自述曰:“《活着.》讲述了一个人和他的命运之间的友情,这是最为感人的友情,他们互相感激,同时也互相仇恨。他们谁也无法抛弃对方,同时谁也没有理由抱怨对方。”这无疑体现了“人性的深度”,却不知不觉中淡化了故事的社会的,体制的背景。而电影所做,恰恰是对这种倾向的一个反动,余华还说:“《活着》讲述了眼泪的丰富与宽广,讲述了绝望的不存在,讲述了人是为了活着本身而活着。”看看,作者几乎是在刻意的回避一些什么。显然他主管上不想让人们对这部作品做过多政治化的解读。
总之,小说通过福贵的叙述多少带些超脱的感觉,而影片则明显带有一种入世的味道。
当然,如果仅从悲剧性角度审视,原作显然更胜一筹,小说当中,福贵所有的亲人都死掉了,他先后亲手埋葬了心爱的为了省鞋光脚跑步的儿子,懂事温顺却苦命加身的聋哑女儿,陪自己走过凄苦一生从来无一句怨言的妻子,在晚年,更致命的打击来临:先是女婿死在建筑工地,其后,活下去的在外人看来唯一的动力————小外孙意外死亡(太饿了,吃豆子撑死了),而他晚年的最好朋友和唯一贴心“人”,就是被他起了“福贵”名字的那头老牛。而电影只却表现了福贵一双儿女的离去,后面三个都特意掩去了,苦根还不叫苦根叫“馒头”,而且大概为了通过“审查”,干脆加上光明的媚俗的尾巴(可即便如此,当局至今年仍然不让这部片子见到天日),引起原作者的不满,也是情理之中的事。可以这么说,电影较之原著,“思想性”增强了,而“悲剧性”却削弱了。生存之道,使他不得不违心的歪曲乃至阉割原著里一些有分量的东西。
值得一提的是,影片对原著的改编,没有停留在机械的重复和照搬上,而是充分运用影像的特征创造充满活力的视觉语言,这也是作品的一大亮点,最有代表性的意象就是皮影。小说压根没提到这类东西,而电影中,它却几乎成了线索性的标志物,是福贵一生坎坷血泪的见证,尤其福贵扯开嗓子那几句唱,可谓愁肠百结神鬼皆惊。虚幻的皮影莫非是惨淡到无味悲凉到无泪的现实的反衬吧?人生如戏,戏梦人生,表面是人在操纵玩偶,实际上人又是块头更大的玩偶而已,极强又极稳妥的象征隐喻意味,使皮影成为改编中的神来之笔。这一点,也如同《菊豆》中大红大黄的染布条,《大红灯笼高高挂》中的红灯笼一样,是编导才气和胆识的体现。
电影中也有不如小说传神的细节,比如表现饥饿。不如小说触目惊心。我读到队长“主持公道”将刨出来的地瓜一分为三,甚至放弃队长的尊严来福贵家讨一小把米回去开饭的情节,心里那种酸楚,的确不是“煽情”的结果。
有批评家认为余华冷静过分,血管里流的不是血而是冰碴,余杰就曾批评它这位本家哥哥,只有肉体的“活着”而没有灵魂的求索,其实我觉得余杰未免言之过苛,把半个世纪以来中国底层民众的真实生存揭示给天下人,不为种种意识形态宣传所左右,以完全的冷静的写实展示苦难,唤起良知,在现今中国文坛,能做到及格水准,四海之大有几人欤?“形而上”的理性反思固然可贵,“形而下”的感性触动却是文学走进民众内心的第一步。
另外,不知电影改编者出于何种考虑,非要把福贵的儿子有庆的死安排为区长的车撞倒围墙砸死,而小说里是为救生孩子难产的县长夫人时硬给抽血抽死的!我看还是原著情节更具震撼力,底层民众的苦难,与权贵们的优越,就是一枚硬币的两面嘛。何况小说里最后写县长在文革中被逼自尽,也多少有种“报应”的影射在里面,在那个年代。谁敢保证自己会逃脱厄运的魔爪?海明威说得好:不要问丧钟为谁而鸣,它就为你敲响!没有基本法治与人权的保障,任何人都在侥幸活着而已。
我想起几年前,一位学生在她的随笔中问我:人活着究竟为了什么,我不假思索地回答:不要问人活着为什么,活着的目的就是活着。也许浸染于年少轻狂的学生并不恭维老师这一太缺乏诗意和“深度”的回答,不过,我相信总有一天她会懂的。
活着就是活着,活着好啊!哪怕只冲“你欠我们家一条命”(福贵夫妇对“误杀”自己儿子的春生如是说)这个理由,我们也得活下去!
对了,这部片子不仅是谋子的巅峰之作,也是演员葛优的最成功作品。他因此荣膺戛纳电影节最佳男主角。可惜因本篇禁映至今令好多人对此并不知情,以为葛优还是那个李东宝那个贺岁片里的“装蛋分子”最多是那个一旦生气后果就很严重的“黎叔”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