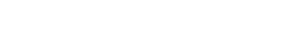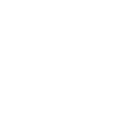《野草莓》:一种心理的影像
?◎片 名 Wild Strawberries
??◎中文 名 野草莓
??◎年 代 1957
??◎国 家 瑞典
??◎类 别 剧情
??◎语 言 瑞典语/拉丁语
??
◎片 长 91 min
??◎导 演 英格玛·伯格曼 Ingmar Bergman
??◎主 演 伊萨克.伯雷 ... Professor Isak Borg
?? 毕比·安德森 Bibi Andersson ... Sara
?? 英格里德·苏琳 Ingrid Thulin ... Marianne Borg
?? Gunnar Bj?rnstrand ... Evald Borg
?? Jullan Kindahl ... Agda
?? Folke Sundquist ... Anders
?? Bj?rn Bjelfvenstam ... Viktor
?? 马克斯·冯·赛多 Max von Sydow ... Henrik ?kerman
?? Naima Wifstrand ... Isak's Mother
一个矛盾重重的人,在内心真实和现实真实之间徘徊与纠缠的人。不知道是现实的冷酷造就了他的冷酷,还是他本性中的温情脉脉,叫现实感受了他的脉脉温情。英格玛•伯格曼的电影,它们的可爱之处在于,当经过了千转百回的内心挣扎之后,最终还是唱了一曲明媚如春的世俗赞歌。西方的影像大师们之所以也能够名垂千古,像陈旧的西方文学大师们那样,是因为他们利用另一种更为直接的方式——视觉和听觉的共同体,让我们见识了这个现实主义的和现代主义的,或是叫做唯物主义的和唯心主义的世界。上帝是用来相信的,也是用来怀疑的,西方人的可爱或可笑之处就在这里。他们的思维特点,和中国人不太一样。西方人不舒服,是由于头脑,我们不舒服,大概是因为身体。自古以来我们没有宗教信仰的历史的根儿,只有现实世界的熨帖和不熨帖。我们不矛盾,我们忍受不了矛盾。我们不怀疑,我们非此即彼。怀疑是什么东西呢?它能当饭吃吗?不信上帝,照旧吃得香;砸烂了孔子的牌坊,仍然不会寝食难安。承传和借鉴,祖宗和外来,或有或无的旁存着,一切为了活着,且要避免陷入思考与自责。
如果把杨德昌的电影叫现象,它引起了我们的思考,那么英格玛•伯格曼的电影可以直接叫做思考,它剧中的人物正做着思考。《野草莓》的主人公伊萨克的思考是在旅途中完成的,而旅途正是这个在专业领域上具有优越感的老者,通过自驾车完成的。汽车也好,火车也好,像美国西部枪战片一样,构成了伯格曼这部电影的运动,它引起了人物的变化,出场和退场的人,他们的语言和行为都在辅助伊萨克情感的变化。旅行的目的是为了获得一个终生成就奖的荣誉,这个目的产生的是影片的空间上的一个终点,但其间伊萨克在时间上的往返,让我们纵观他的一生。空间上的伪高潮,也就是老人具体获得的荣誉的事,相对于老人时间上所做的跨越——回忆与领悟——而言,几乎是微不足道的。我们的追求了表面的,而失去的却是最深厚的。
这个老头没有信仰危机,倒不是因为他是个医生,具有自发的唯物主义信念。而是,他采取了一种狡猾的规避的态度,或者也可以叫作逃避。梦中的那张死一样难看的五官努力挤在一起的没有表情的脸,就是他内心之写照。不探究人与上帝之间形而上的联系,更不会去探究人与人之间形而下的关系。这位七十多岁的古来稀,除了业务上的需要,才过问别人之外,他从不以为爱的关系是一种真实的存在。他丧失了任何爱的能力。作为医生,“整个村子都在谈论他”和感激他,然而在加油站的那一刻,我们看到,伊萨克答非所问地,为爱娃俩口子的热情而感到局促不安。作为家人,他并不是那种伤害手足的坏人,但他的确是个冷血动物。从某种意义上讲,他是一个清高的不懂人情世故的老头。所以,看这部电影的前提是,需要我们去读解他,而不是让他来读解我们,而他对人,对我们的理解,完全是不差毫厘的,生活就是充满了欺骗和背叛。我见过的所有影评当中,都设定了一种恶俗的价值,伊萨克好象是被人们拯救的。实际上是,即便他没有拯救我们——也难以拯救,但他宽宥了我们。“是现实的冷酷造就了他的冷酷,还是他本性中的温情脉脉,叫现实感受了他的脉脉温情”——我不得不引用我开头造的这个句子。
伊萨克的问题是,他无法在现实中实现一段纯真之爱,又始终不会放弃自我,依靠一个对上帝的信念。被他钟爱的女孩名叫莎拉。年轻的时候,伊萨克就在女孩和上帝之间选择了女孩。《野草莓》不是言情剧,剧情是个危险的东西:不是往昔的他在她那里受挫,变成了日后的他,而是他必定会受挫。女人是现实之物,而他是个柏拉图似的精神怪物。给女人写诗,不如调戏她,你越尊重她,她就越假惺惺。《燃情岁月》里的卓斯顿,建议森姆直接把未婚妻干了;而北村的小说《玛卓的爱情》中,写了三年情书的男人刘仁,根本无法和女人实际地生活。伊萨克没有出现在叔叔的家庭聚会上,他少年时代的影像是缺失的,他早已养成了离群索居的性格。
从电影语言上讲,英格玛•伯格曼的电影是不难懂的。他对电影语言不能算做过什么创新之举。最早接触英格玛•伯格曼,是通过他的一部剧本选集,里面有《夏夜的微笑》、《第七封印》、《野草莓》等等,读了剧本,就能知道他想表达什么。电影我只看过三部:《第七封印》、《处女泉》、《野草莓》。不过分的说,他所有的电影都可以改编成话剧。电影只不过给了他一个空间和时间上的便利,也许戏剧对他更有好处,电影是不是有损于他思想的表达呢,这尚是个不定之数和一家之言。自然伯格曼的镜头是非常精致的,让我惊讶的是,英格玛•伯格曼能把下一个特写直接和上一个大全景剪切在一起。正是他那特有的思维,以及外部环境与内心的直接冲撞,让这种剪辑方式显得毫不造作。《野草莓》里有这样一个例子,梦中的伊萨克在靠近墙壁的地方来回走动,镜头跟着他,向明亮处走去,又返头走回阴影处,摄影机是移动的,而且景别很大,下个镜头是脸部的大特写,摄影机是静止的,伊萨克是运动着入画的,是动接动,动作以及影调都衔接的天衣无缝。
对于一个贯通西方文学或西方哲学史的人,英格玛•伯格曼并不是晦涩的。从家庭背景和人文背景,我们能轻而易举地阐释他。晦涩的是英格玛•伯格曼选择了影像来表达。似乎他建立了一种心理上难以言传的影像。这种影像从基耶斯洛夫斯基的《十戒》里也可以看到。他们之所以成为电影大师,到底是和表达的内容有关呢,还是和电影本身有关呢?或者是,大师们所选择的,叫他们的头脑感觉极不熨帖的内容,最终令电影有所延伸呢?
?◎片 名 Wild Strawberries
??◎中文 名 野草莓
??◎年 代 1957
??◎国 家 瑞典
??◎类 别 剧情
??◎语 言 瑞典语/拉丁语
??
◎片 长 91 min
??◎导 演 英格玛·伯格曼 Ingmar Bergman
??◎主 演 伊萨克.伯雷 ... Professor Isak Borg
?? 毕比·安德森 Bibi Andersson ... Sara
?? 英格里德·苏琳 Ingrid Thulin ... Marianne Borg
?? Gunnar Bj?rnstrand ... Evald Borg
?? Jullan Kindahl ... Agda
?? Folke Sundquist ... Anders
?? Bj?rn Bjelfvenstam ... Viktor
?? 马克斯·冯·赛多 Max von Sydow ... Henrik ?kerman
?? Naima Wifstrand ... Isak's Mother
一个矛盾重重的人,在内心真实和现实真实之间徘徊与纠缠的人。不知道是现实的冷酷造就了他的冷酷,还是他本性中的温情脉脉,叫现实感受了他的脉脉温情。英格玛•伯格曼的电影,它们的可爱之处在于,当经过了千转百回的内心挣扎之后,最终还是唱了一曲明媚如春的世俗赞歌。西方的影像大师们之所以也能够名垂千古,像陈旧的西方文学大师们那样,是因为他们利用另一种更为直接的方式——视觉和听觉的共同体,让我们见识了这个现实主义的和现代主义的,或是叫做唯物主义的和唯心主义的世界。上帝是用来相信的,也是用来怀疑的,西方人的可爱或可笑之处就在这里。他们的思维特点,和中国人不太一样。西方人不舒服,是由于头脑,我们不舒服,大概是因为身体。自古以来我们没有宗教信仰的历史的根儿,只有现实世界的熨帖和不熨帖。我们不矛盾,我们忍受不了矛盾。我们不怀疑,我们非此即彼。怀疑是什么东西呢?它能当饭吃吗?不信上帝,照旧吃得香;砸烂了孔子的牌坊,仍然不会寝食难安。承传和借鉴,祖宗和外来,或有或无的旁存着,一切为了活着,且要避免陷入思考与自责。
如果把杨德昌的电影叫现象,它引起了我们的思考,那么英格玛•伯格曼的电影可以直接叫做思考,它剧中的人物正做着思考。《野草莓》的主人公伊萨克的思考是在旅途中完成的,而旅途正是这个在专业领域上具有优越感的老者,通过自驾车完成的。汽车也好,火车也好,像美国西部枪战片一样,构成了伯格曼这部电影的运动,它引起了人物的变化,出场和退场的人,他们的语言和行为都在辅助伊萨克情感的变化。旅行的目的是为了获得一个终生成就奖的荣誉,这个目的产生的是影片的空间上的一个终点,但其间伊萨克在时间上的往返,让我们纵观他的一生。空间上的伪高潮,也就是老人具体获得的荣誉的事,相对于老人时间上所做的跨越——回忆与领悟——而言,几乎是微不足道的。我们的追求了表面的,而失去的却是最深厚的。
这个老头没有信仰危机,倒不是因为他是个医生,具有自发的唯物主义信念。而是,他采取了一种狡猾的规避的态度,或者也可以叫作逃避。梦中的那张死一样难看的五官努力挤在一起的没有表情的脸,就是他内心之写照。不探究人与上帝之间形而上的联系,更不会去探究人与人之间形而下的关系。这位七十多岁的古来稀,除了业务上的需要,才过问别人之外,他从不以为爱的关系是一种真实的存在。他丧失了任何爱的能力。作为医生,“整个村子都在谈论他”和感激他,然而在加油站的那一刻,我们看到,伊萨克答非所问地,为爱娃俩口子的热情而感到局促不安。作为家人,他并不是那种伤害手足的坏人,但他的确是个冷血动物。从某种意义上讲,他是一个清高的不懂人情世故的老头。所以,看这部电影的前提是,需要我们去读解他,而不是让他来读解我们,而他对人,对我们的理解,完全是不差毫厘的,生活就是充满了欺骗和背叛。我见过的所有影评当中,都设定了一种恶俗的价值,伊萨克好象是被人们拯救的。实际上是,即便他没有拯救我们——也难以拯救,但他宽宥了我们。“是现实的冷酷造就了他的冷酷,还是他本性中的温情脉脉,叫现实感受了他的脉脉温情”——我不得不引用我开头造的这个句子。
伊萨克的问题是,他无法在现实中实现一段纯真之爱,又始终不会放弃自我,依靠一个对上帝的信念。被他钟爱的女孩名叫莎拉。年轻的时候,伊萨克就在女孩和上帝之间选择了女孩。《野草莓》不是言情剧,剧情是个危险的东西:不是往昔的他在她那里受挫,变成了日后的他,而是他必定会受挫。女人是现实之物,而他是个柏拉图似的精神怪物。给女人写诗,不如调戏她,你越尊重她,她就越假惺惺。《燃情岁月》里的卓斯顿,建议森姆直接把未婚妻干了;而北村的小说《玛卓的爱情》中,写了三年情书的男人刘仁,根本无法和女人实际地生活。伊萨克没有出现在叔叔的家庭聚会上,他少年时代的影像是缺失的,他早已养成了离群索居的性格。
从电影语言上讲,英格玛•伯格曼的电影是不难懂的。他对电影语言不能算做过什么创新之举。最早接触英格玛•伯格曼,是通过他的一部剧本选集,里面有《夏夜的微笑》、《第七封印》、《野草莓》等等,读了剧本,就能知道他想表达什么。电影我只看过三部:《第七封印》、《处女泉》、《野草莓》。不过分的说,他所有的电影都可以改编成话剧。电影只不过给了他一个空间和时间上的便利,也许戏剧对他更有好处,电影是不是有损于他思想的表达呢,这尚是个不定之数和一家之言。自然伯格曼的镜头是非常精致的,让我惊讶的是,英格玛•伯格曼能把下一个特写直接和上一个大全景剪切在一起。正是他那特有的思维,以及外部环境与内心的直接冲撞,让这种剪辑方式显得毫不造作。《野草莓》里有这样一个例子,梦中的伊萨克在靠近墙壁的地方来回走动,镜头跟着他,向明亮处走去,又返头走回阴影处,摄影机是移动的,而且景别很大,下个镜头是脸部的大特写,摄影机是静止的,伊萨克是运动着入画的,是动接动,动作以及影调都衔接的天衣无缝。
对于一个贯通西方文学或西方哲学史的人,英格玛•伯格曼并不是晦涩的。从家庭背景和人文背景,我们能轻而易举地阐释他。晦涩的是英格玛•伯格曼选择了影像来表达。似乎他建立了一种心理上难以言传的影像。这种影像从基耶斯洛夫斯基的《十戒》里也可以看到。他们之所以成为电影大师,到底是和表达的内容有关呢,还是和电影本身有关呢?或者是,大师们所选择的,叫他们的头脑感觉极不熨帖的内容,最终令电影有所延伸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