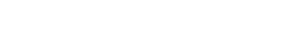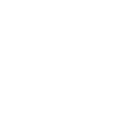《杀人回忆》的隐喻——当历史毁灭真相
一、蒙眼的正义女神
在希腊神话的“青铜时代”中,世界不再祥和美好,而是充满谎言、暴力、血腥,人们一步步走向罗网和罪孽。正义女神狄刻手中那衡量正义与邪恶的天平不堪重负,她的同伴“羞耻”和“敬畏”两位女神甚至无法忍受这样的景象,终于抛弃了人类,回到奥利匹斯山上加入永生神灵的行列,只留下她身披云雾愤怒地在城市上空飞行。从此,人类将自食恶果,陷入“黑铁时代”,用谎言欺骗狄刻女神的人将不仅给自己也给自己的城市带来灾祸。时至今日,每当遇见不平,人们仍旧会想起那个主持正义的女神:在狄刻那里,贿赂和求饶不起任何作用,她蒙起双眼,以示对世间万物一视同仁,不受感情的蒙蔽;她左手持天平,掩饰再好的罪恶放在上面都昭然若揭;她右手持利剑,任何逍遥作恶的人或事都会成为剑下的祭品。
在西方电影中,一直遵从着“善恶终有报”(Be Sure your sin will find you out)的原则,不论多么强大的势力和狡猾的手段,终究逃不出法律公正的制裁。在弗朗西斯•科波拉导演的“造雨人”(The Rainmaker)中,马特•达蒙扮演了初出茅庐的律师鲁迪•贝勒,他年轻气盛,正义感十足,凭着良知和主持公道的精神,揭露了实力雄厚的保险公司的阴谋,为一直无法索赔的受害者讨还了一份公道。在电影中,青涩且学识尚浅的鲁迪•贝勒面对制定当今法律的那些律师界泰斗人物的威逼利诱,仍旧不敢初衷,难怪在很多人眼里他简直就是“鸡蛋碰石头”,自讨没趣。但是正义总是站在手持真理的少数人这边的,你说这是美好的愿望也好,奇迹也罢,鲁迪打赢了官司。不过,他打赢的也只是一场官司,那些左右判决和玩弄权势的人仍旧存在且不可撼动。好在电影留给人希望:只要去争取,坚持信念,少数弱者也会赢得胜利。这种坚信隐藏再好的罪恶总会如影随形的精神,在“灵数23”(The Nember23)中体现得更加淋漓尽致。虽然人们都说时间可以抹去一切,记忆可以选择性的把不好的回忆埋葬,沃尔特•斯派格在13年前犯下的罪行仍旧再次找上了他,有些血债总是要偿还的。
除却这些正统沿袭以上精神的电影,还有一些是反其道行之的。“杀人回忆”就是典型一例让人陷入无底哀伤和前所未有般无助的作品。电影以上个世纪八十年代韩国民主化前夕的骚动和暴乱为背景,讲述了发生在乡下的一起连环奸杀案件。
故事从麦浪翻滚、一望无际的田地开始,顽皮的孩子蹑手蹑脚地捕捉着麦尖的蚂蚱,对于他们来说,这是存活在回忆中最鲜明美好的年代。镜头眯着眼睛,画面呈现一种遥远似梦境的美感。孩子们嬉笑、跳跃的追逐着吭吱作响的拖拉机,坐在车上的朴多曼警官若有所思,不耐烦地回应着孩子们的嘲笑。在麦田一旁的沟渠中,朴警官必须使劲弯下身才能看到全身赤裸、双手反绑的女尸,女尸身上密密麻麻地爬满了黑色的虫子,感觉到有光照过来,它们就哗啦一声四散而去。朴警官站起身,心情很差,咒骂着远处吵闹的孩子。他还不知道这个日子将会具有什么样的意义,1986年10月23日,他的生命从此改变。
追溯到几百年前,判定一个人是否有罪,多数倚赖于对嫌疑犯的严刑逼供,炮烙、宫刑、刖刑、黥刑、车裂等许多血腥暴力的刑罚也应运而生,一些无辜的人轻则终身残废重则被推上了绞刑架。1764年,意大利刑法学家贝卡利亚无法再忍受这样泯灭人性的血影寒光,提出了“无罪推定”的构想,即“在法官判决之前,一个人是不能被称为罪犯的。”这一人性化的原则被运用到了现代国际上的审讯中,以此避免了诸多冤假错案的发生。
在“杀人回忆”中,朴多曼警官显然对维护个人权利这一说法并不在乎,每次揪来嫌疑人都是一顿劈头盖脸的审讯,不给对方任何辩解的机会,直接就破口大骂,指责对方无耻的杀人罪行,并引诱嫌疑人展露对受害者越轨的情欲需求。朴多曼把嫌疑人的照片贴了满满几页纸,自信满满地跟别人说自己有一双能读懂人的眼睛,可以看出谁是罪犯。于是,在搜集了一些所谓线索后,他断定喜欢跟踪受害者的白光昊就是头等嫌疑人,或者说白光昊就是罪犯更准确。朴多曼剩下的工作就是逼光昊承认自己的罪行。在普通人眼里,光昊只是个可怜的弱智儿,身材矮小,其貌不扬,脸上还有一块被火烫伤的伤疤。人们都知道,他双手萎缩得连绑绳子的力气都没有,怎么可能是精心策划不留一丝痕迹的杀人犯呢?可我们的警察先生可看不到这些,脾气暴躁的乔勇谷警官上来就是一个利落的飞踹,把光昊放倒在地,一边狠狠地踹着光昊还一边嘟囔着“你的脸恶心死了”。
每当雾气蒙蒙,雨天来临,村子里就人心惶惶,没人敢穿红色衬衣出门,空气中弥漫着阴气森森的死亡。来自汉城的高级警官徐太允,被惊弓之鸟的女人指为强奸犯,白白挨了朴多曼的一顿胖揍。对此,徐太允只能认倒霉的撇撇嘴,嘲弄朴多曼,哪里见过像他这么辨不清黑白的警察?徐太允是高材生,脑子十分灵光。他有着侦探小说中传奇警探的头脑,一切按照证据,顺藤摸瓜,从失踪人名单中就能发现谁是下一个受害者,并阻止了朴多曼对两个嫌疑人的屈打成招。有这样的警察无懈可击地理智办案,案件的侦破仿佛指日可待。
随着雨季的来临,降雨的频繁,受害者也逐渐增多,犯人的手法也愈加地嚣张残忍,一点也不将警察的追捕放在眼里。朴多曼和徐太允因为办案理念不同,两人之间频频摩擦,以致大打出手。犯罪的猖狂让每个人都坐如针毡,失去耐性,变得躁狂、绝望。当一切线索都指向一个工厂技工朴兴圭,每个警察都兴奋起来,迫不及待的要定他的罪。的确,朴兴圭具有一切他们所掌握的犯人的特点,但是他们仍旧缺乏证据。就在他们无奈放走朴兴圭的当晚,又一起犯罪事件发生了,发生得如此迅速,仿若只用了战栗的瞬间。而这次的受害者,还只是个孩子。就在前一日徐太允还和这个孩子谈笑风生。他失去了理智,找出了朴兴圭,怒吼着对他拳打脚踢,逼迫对方露出真面目。就在这时,朴多曼拿来了嫌疑人的DNA检验报告,结果显示朴兴圭并非罪犯。徐太允的世界崩塌了,一切按部就班的推理竟然换来了如此的结局,他不肯相信这个结果,举枪射向了朴兴圭。
朴多曼在亲眼目睹光昊因为对警察惧怕而被火车撞死的惨状后,开始重新审视自己的人生。他辞去了警官的职务,去汉城当了推销员,过上了平静富足的生活。
2003年,他因为工作路过当年的村庄。一切似乎都未改变过,一样金黄翻涌的麦田,一样宁静的午后,不同的是当他使劲弯下腰看向沟渠深处时,再未看到女尸。朴多曼摘下了眼镜,仿佛在穿越时间望向回忆的深处。一个学生路过这里,好奇地询问朴多曼在看什么,她说前几天也有一个男人也蹲在这里看,说是想起以前在这里做过的事情。
微风吹过麦田,这个声音一直在朴多曼的记忆中沙沙作响,时间仿佛在这一刻凝固了。他忍住了眼泪,小心翼翼地询问那个男人的长相,眼神中再次掺杂了某种希望。而女孩只能告诉他,那个人就是普通的样子。
仿佛有颗石子沉重的落入朴多曼的心中,他无助地四下张望。那垂死的希望,呻吟了两声再次被践踏蹂躏直至无声哽咽。朴多曼眼含热泪望着镜头,眼中是无底的深渊。
在金基德的影片中,主角多半是哑巴或者不愿说话的人。无论是“坏小子”(Bad Guy)中暗恋女大学生的哑巴,还是“空房间”中那个一语不发喜欢潜入陌生人房间的青年,抑或是“弓”(The Bow)中几乎一片空白的台词。这样的设置都让金基德的影片有种压抑中蓄势待发的无言力量,导演在平静中寻求呐喊,就像吴宇森在静止的画面中表现速度一般精妙。正如只有白昼才能衬托黑暗的力量,只有磨难才能衬托美德的光辉,他们都用极致的对比手法展现更加强大的镜头语言。
“杀人回忆”的导演奉俊昊让镜头中的每个人都变成“盲人”,让他们在无边的黑暗中永远看不见凶手。警官找到的每条线索都看似有理,却总会在关键时刻将他们引入歧途,白忙一场。那些见过凶手的人,要不就是弱智,要不就是孩子,没人能告诉他们罪犯的相貌。那张脸就像芸芸众生中的任何一张脸,就像大海中的一滴水,无从找寻。导演运用这样无所适从的设置手法,让观众和故事中的每一个人一样陷入无法自拔的深渊,带着永不可及的绝望哀号、哭泣。这样的感觉正贴合了经历了上世纪八十年代韩国人的心理,这就不难解释为何电影一经上映便蝉联数周票房冠军,并获得多项大奖。那时候,韩国民众还在民主制的初期挣扎,在压抑中充满绝望地反抗着,看不到未来的曙光。电影中随处可见群众对政府的不满,民众在军队统治压迫下的恐惧。
导演让蒙眼的正义女神变成了瞎眼的正义女神。好人一次次倒在死亡的镰刀下,坏人却可以逍遥作案,甚至在多年后重游故地,悠然欣赏自己当年的“杰作”。
那么,是不是这个世界真的就没有正义可言了?我只能说,正义不是像好莱坞电影中好人最终取得胜利,坏人得到应有的惩罚。毕竟,正义女神没有火眼金睛,她只负责衡量和判决,捉拿罪犯不在她的职责范围内。在影片中,并没有任何一个无辜的嫌疑人冤死。就在电影末尾,徐太允警官崩溃的举枪要射杀朴兴圭的那一刻,想必很多观众不管朴兴圭是否有罪,也希望徐太允将他先杀而后快了,毕竟许久的压抑,谁都希望有个人来承担这份罪行。但是,正义女神没有让他的子弹偏差失准,每一枪都命中墙壁,也没有让飞驰的火车轧过朴兴圭的身体,他最终只是踉踉跄跄的隐入隧道的深处。
正义女神不负责追捕,只负责审判。她不能撒下天网,却清楚地知道面对嫌疑人,正义的剑该何时砍下,何时归入剑鞘。
二、奉俊昊的政治隐喻
奉俊昊之所以只拍了三部电影就可以跻身一线导演的行列,名利双收,不仅在于他纯熟的镜头语言,也因为他影片中的政治隐喻,道出了广大韩国民众的呼声。
虽然韩国已经实现了民主制,但是在他们的民族性格中,很多东西早已根深蒂固,不可扭转。例如等级分明,崇尚权威。在“不可不信缘”中,高一个年级的师兄就可以命令、呵斥甚至抡起木棍毒打学弟,无论谁称呼比自己年龄大的人都要用敬语。在“杀人回忆”中,警官问话审讯的时候,没有一个人敢质疑反抗,都是老老实实地挨骂受训。这是韩国人民族性格中不可磨灭的东西,也是造成他们压抑痛苦的根源。这种矛盾的痛苦在奉俊昊的电影中体现的尤为明显。
电影中有一个细节:白光昊被拷打的间歇,和朴多曼、乔勇谷警官一起吃饭,观看颂扬警察神勇破案的电视剧。白光昊兴奋的大叫,说这个电视节目是自己最喜欢看的,要给爸爸打电话告诉他。乔勇谷好脾气的劝他不要那么多话,好好吃饭。三个人之间的气氛简直可以用诡异的其乐融融来形容,谁能想象刚才其中一个人还在遭受毒打?警察这个角色在“杀人回忆”中代表的正是一种强权,这种强权的压力往往来自韩国政府。民众一方面觉得政府像警察对罪犯私刑拷打一样剥夺民众的人权,另一方面又景仰这种强权,感觉受到保护,就像白光昊喜欢看那个有关警察的电视剧一样。不光是韩国人,很多人都有这种对强权的依赖,也许这是人们的惰性和奴性使然,中国人不是有句古话么,“背靠大树好乘凉”,正是应证了这一说法。人的力量太渺小了,总希望依靠强大的力量寻求保护。
在故事中,警官对案件的查询仿佛总会受到来自群众的阻挠。比如,徐太允打电话询问电台点歌者的地址,他们却认为这是一个恶作剧挂断了电话;朴多曼依照自己的断定,去澡堂查询男子的下体,遭到了澡堂老板的嘲笑;警官在勘查犯罪现场的时候,经常会被破坏现场的群众打乱阵脚。警察抓罪犯是为了民众的出行安全,却得不到民众的支持,反而可以看到每次抓到一个嫌疑人,都会有大批的群众在警察局门口示威游行,抗议警察铐打嫌疑人或者咒骂他们低能的抓错了人。这充分体现了民众对政府的怀疑,有些怀疑是有根有据的,有些怀疑却是毫无来由的。正是这种互相的不信任,导致了罪犯最终逍遥法外,使得受害人死不瞑目。
高级警察徐太允的出现仿佛和当地保守落后的气氛不符合,他就像一剂强心针,给警队注入了全新的思考模式和活力。他和朴多曼,分别代表着韩国想要革新的一派和仍旧落后守旧的一派。他们一个相信理智断案,一个相信感觉。但随着事情的发展,两人的心理也逐渐发生了变化:朴多曼亲眼见到白光昊因为惧怕警察而惨死,开始反思自己的断案方式,反思自己一直以来心安理得奉行的原则是否正确?而徐太允从一开始的志得意满,到后来发现自己的一切努力都是白费,熟识的女孩在一夜之间就变成了地上冰冷的女尸。他的世界观全盘崩溃,他发现与其一步步照章办事,有理有据,不如一枪崩了那个坏蛋来得简单解恨,如果早就这么办,女孩也许就不会死了。就算当证据又一次告诉他,他的推测是错误的,他宁愿相信DNA的检验结果是错的,也不愿意再相信这个疯狂的世界有什么理智可言了。徐太允和朴多曼两人的遭遇和感情变迁,也从某方面影射了韩国当时两派势力的斗争。他们都坚信自己可以让国家更加和谐繁荣,而在斗争辩论的过程中,他们又都变得迷茫,不再坚持初衷,对现实妥协。
除了朴多曼和徐太允警官,电影中还有一个引人注目的警察乔勇谷。他擅长各种飞踹和拷打罪犯方式,每当朴多曼不想问下去了,就挥一挥手示意,乔勇谷就会义无反顾地扑上去把对方踢倒,一顿暴打。这个人物虽然暴力,但也有他正直的一面,比如他对工作兢兢业业,追逐疑犯的时候锲而不舍,受伤的时候也不大呼小叫,只是冷静的把钉子从腿上拔出来。这些其实都是值得赞许的军人精神,也是当时军政府统治值得称赞的一面。但是,事态的演变就好比那段因扎上生锈钉子而需要截肢的右腿,当他的做法不再符合现实世界的发展,就要忍痛割去,才能继续存活。这就是韩国需要废除军人统治才能继续更好发展的最终结果。
电影中还有很多诸如此类值得玩味的细节。比如伫立在稻田边那个穿红衣的稻草人。稻草人本来是用来吓唬偷食谷稻的小鸟的,人们让它穿上罪犯喜欢的红色衬衣,正是想借此转移罪犯的注意力。但是,谁都知道这是掩耳盗铃的做法,毫无用处,只能给自己几分心理安慰。也从另一个侧面,显示了社会的动荡不安,人们无力改变这一切,只好把希望托付给一个毫无用处的稻草人。
三、祈祷还是反抗?
“杀人回忆”中那个残暴聪明的杀人犯就像一种不可预知的强大力量,每个人面对他最终都会手足失措,毫无还击的余地。人们只能眼睁睁的看着他躲在墓地的后面,偷偷窃笑。这是人们对某种未知力量的恐惧,对那种浓郁浑浊的黑暗充满恐惧。
在奈特•沙马兰导演的“天兆”(Signs)中,当麦田圈大面积的出现在世界各个角落时,人们只能瞪着眼睛,守着电视,看着外星人的飞船一片片占据了天空,尖叫着四处奔逃。面对如此前所未有的景象,人们纷纷聚集在教会、教堂、寺庙,电视上的主持人也只能祈祷“愿上帝与我们同在”。
而在另一部韩国影片“奥罗拉公主”中,导演则持有不同的态度。严贞花扮演的郑顺贞看似是一名敬业努力的汽车销售员,实际上是为死去的女儿复仇的战士,她心中的痛苦像条毒蛇每天啃噬她的心,让她心中的怒火越烧越旺。郑顺贞的女儿一年前被一个恋童癖男人奸杀之后,当作垃圾一样丢到了垃圾场。而那个该千刀万剐的男人竟然在律师的庇护下,辩解自己神经失常,逃离了法律的制裁。郑顺贞的丈夫吴警官虽然身为警察,却只能坐视罪犯玩弄法律于股掌。面对无法挽回的事实,他选择平静祈祷,立志去做一个牧师。
郑顺贞精心策划,让每一个造成女儿悲惨下场的人都不得好死。而那几个人都代表了平日社会里一种不公平的现象,郑顺贞就以复仇女神的名义将他们一个个铲平。眼见妻子豁出性命为女儿奋不顾身,血流成河,撕心裂肺的哀号,吴警官就像一个醉酒的人挨了一闷棍猛醒过来,辞去了警察的工作,继续妻子未完成的复仇。
前共和党发言人纽特•格林威治在评价“星球大战”的时候,曾说过,“站在正确一方的弱者打败了站在错误一方的强者,这是一种根深蒂固的美国神话”,换言之就是胜利永远属于正义的一方。不过,对于大多数人来说,很难想象自己是那个击败大人物的英雄,毕竟那些都是小说和电影中塑造的英雄形象,而诞生的英雄数量在历史中,肯定要远远少于死于邪恶魔爪下的人,更多冲锋陷阵的人都是充当了寂寂无名炮灰。所以,绝对的说,面对危机我们该祈祷还是反抗都是缺乏说服力的。
我不能说“奥罗拉公主”中郑顺贞的做法是正确的。作为一个母亲,她是值得人尊敬敬畏的,但是作为一个人,她没有权利决定他人的生死,更何况她杀的一些人实际上罪不至死。我想,导演更多的还是想表现对社会不公平现象的不满。
能被大多数人理解并接受的观念,还是“世界大战”(War of the Worlds)中那个汤姆•克鲁斯所饰演的码头工人雷•费瑞尔形象。费瑞尔年纪轻轻就有了两个孩子,离过一次婚,但这并没有增加他责任心,他仍旧整天游手好闲,追求物质上的享受。当外星人来袭,他只得抱着女儿,领着儿子开始他们的逃亡生涯。在这中间,他们经历了争吵和信任危机,儿子离开了他去反抗外星人,他则孤注一掷的守着女儿,在一次又一次的生死关头,费瑞尔心中对女儿的责任感被唤醒。为了女儿,他杀死了那个精神失常险些暴露他们的人;在外星人抓走女儿后,急中生智的捡起地上的手榴弹塞进外星人的内核。在外人看来,这是英雄事迹,而对他来说,他只是为了保护女儿。
战胜邪恶这个信念对于大多数人来说,固然理想远大但是遥不可及,但是守护家人是很多人都会去做,而且常常会因此创造奇迹。
在“杀人回忆”中,朴多曼夸耀自己的眼光犀利,能分辨出罪犯时,局长曾经问他,有一个强奸未遂的男人和受害者的哥哥都在写笔供,让他看到底哪个人是罪犯。导演并未让朴多曼作出判断,就像那个无法结案的连环杀人案件。
有些真相会被时间的车轮碾过,被历史的风沙掩埋,人们能做的不是去追究无谓的结果。很多事情冥冥之中自有定数,就像“天兆”中,儿子的哮喘、女孩的洁癖还有母亲的去世都预示着未来发生的事情,很多结果不是我们很快就能看到的。我们能做的,就像那个保护女儿的父亲那样尽力而为,看看生活给我们怎样的答复。
一、蒙眼的正义女神
在希腊神话的“青铜时代”中,世界不再祥和美好,而是充满谎言、暴力、血腥,人们一步步走向罗网和罪孽。正义女神狄刻手中那衡量正义与邪恶的天平不堪重负,她的同伴“羞耻”和“敬畏”两位女神甚至无法忍受这样的景象,终于抛弃了人类,回到奥利匹斯山上加入永生神灵的行列,只留下她身披云雾愤怒地在城市上空飞行。从此,人类将自食恶果,陷入“黑铁时代”,用谎言欺骗狄刻女神的人将不仅给自己也给自己的城市带来灾祸。时至今日,每当遇见不平,人们仍旧会想起那个主持正义的女神:在狄刻那里,贿赂和求饶不起任何作用,她蒙起双眼,以示对世间万物一视同仁,不受感情的蒙蔽;她左手持天平,掩饰再好的罪恶放在上面都昭然若揭;她右手持利剑,任何逍遥作恶的人或事都会成为剑下的祭品。
在西方电影中,一直遵从着“善恶终有报”(Be Sure your sin will find you out)的原则,不论多么强大的势力和狡猾的手段,终究逃不出法律公正的制裁。在弗朗西斯•科波拉导演的“造雨人”(The Rainmaker)中,马特•达蒙扮演了初出茅庐的律师鲁迪•贝勒,他年轻气盛,正义感十足,凭着良知和主持公道的精神,揭露了实力雄厚的保险公司的阴谋,为一直无法索赔的受害者讨还了一份公道。在电影中,青涩且学识尚浅的鲁迪•贝勒面对制定当今法律的那些律师界泰斗人物的威逼利诱,仍旧不敢初衷,难怪在很多人眼里他简直就是“鸡蛋碰石头”,自讨没趣。但是正义总是站在手持真理的少数人这边的,你说这是美好的愿望也好,奇迹也罢,鲁迪打赢了官司。不过,他打赢的也只是一场官司,那些左右判决和玩弄权势的人仍旧存在且不可撼动。好在电影留给人希望:只要去争取,坚持信念,少数弱者也会赢得胜利。这种坚信隐藏再好的罪恶总会如影随形的精神,在“灵数23”(The Nember23)中体现得更加淋漓尽致。虽然人们都说时间可以抹去一切,记忆可以选择性的把不好的回忆埋葬,沃尔特•斯派格在13年前犯下的罪行仍旧再次找上了他,有些血债总是要偿还的。
除却这些正统沿袭以上精神的电影,还有一些是反其道行之的。“杀人回忆”就是典型一例让人陷入无底哀伤和前所未有般无助的作品。电影以上个世纪八十年代韩国民主化前夕的骚动和暴乱为背景,讲述了发生在乡下的一起连环奸杀案件。
故事从麦浪翻滚、一望无际的田地开始,顽皮的孩子蹑手蹑脚地捕捉着麦尖的蚂蚱,对于他们来说,这是存活在回忆中最鲜明美好的年代。镜头眯着眼睛,画面呈现一种遥远似梦境的美感。孩子们嬉笑、跳跃的追逐着吭吱作响的拖拉机,坐在车上的朴多曼警官若有所思,不耐烦地回应着孩子们的嘲笑。在麦田一旁的沟渠中,朴警官必须使劲弯下身才能看到全身赤裸、双手反绑的女尸,女尸身上密密麻麻地爬满了黑色的虫子,感觉到有光照过来,它们就哗啦一声四散而去。朴警官站起身,心情很差,咒骂着远处吵闹的孩子。他还不知道这个日子将会具有什么样的意义,1986年10月23日,他的生命从此改变。
追溯到几百年前,判定一个人是否有罪,多数倚赖于对嫌疑犯的严刑逼供,炮烙、宫刑、刖刑、黥刑、车裂等许多血腥暴力的刑罚也应运而生,一些无辜的人轻则终身残废重则被推上了绞刑架。1764年,意大利刑法学家贝卡利亚无法再忍受这样泯灭人性的血影寒光,提出了“无罪推定”的构想,即“在法官判决之前,一个人是不能被称为罪犯的。”这一人性化的原则被运用到了现代国际上的审讯中,以此避免了诸多冤假错案的发生。
在“杀人回忆”中,朴多曼警官显然对维护个人权利这一说法并不在乎,每次揪来嫌疑人都是一顿劈头盖脸的审讯,不给对方任何辩解的机会,直接就破口大骂,指责对方无耻的杀人罪行,并引诱嫌疑人展露对受害者越轨的情欲需求。朴多曼把嫌疑人的照片贴了满满几页纸,自信满满地跟别人说自己有一双能读懂人的眼睛,可以看出谁是罪犯。于是,在搜集了一些所谓线索后,他断定喜欢跟踪受害者的白光昊就是头等嫌疑人,或者说白光昊就是罪犯更准确。朴多曼剩下的工作就是逼光昊承认自己的罪行。在普通人眼里,光昊只是个可怜的弱智儿,身材矮小,其貌不扬,脸上还有一块被火烫伤的伤疤。人们都知道,他双手萎缩得连绑绳子的力气都没有,怎么可能是精心策划不留一丝痕迹的杀人犯呢?可我们的警察先生可看不到这些,脾气暴躁的乔勇谷警官上来就是一个利落的飞踹,把光昊放倒在地,一边狠狠地踹着光昊还一边嘟囔着“你的脸恶心死了”。
每当雾气蒙蒙,雨天来临,村子里就人心惶惶,没人敢穿红色衬衣出门,空气中弥漫着阴气森森的死亡。来自汉城的高级警官徐太允,被惊弓之鸟的女人指为强奸犯,白白挨了朴多曼的一顿胖揍。对此,徐太允只能认倒霉的撇撇嘴,嘲弄朴多曼,哪里见过像他这么辨不清黑白的警察?徐太允是高材生,脑子十分灵光。他有着侦探小说中传奇警探的头脑,一切按照证据,顺藤摸瓜,从失踪人名单中就能发现谁是下一个受害者,并阻止了朴多曼对两个嫌疑人的屈打成招。有这样的警察无懈可击地理智办案,案件的侦破仿佛指日可待。
随着雨季的来临,降雨的频繁,受害者也逐渐增多,犯人的手法也愈加地嚣张残忍,一点也不将警察的追捕放在眼里。朴多曼和徐太允因为办案理念不同,两人之间频频摩擦,以致大打出手。犯罪的猖狂让每个人都坐如针毡,失去耐性,变得躁狂、绝望。当一切线索都指向一个工厂技工朴兴圭,每个警察都兴奋起来,迫不及待的要定他的罪。的确,朴兴圭具有一切他们所掌握的犯人的特点,但是他们仍旧缺乏证据。就在他们无奈放走朴兴圭的当晚,又一起犯罪事件发生了,发生得如此迅速,仿若只用了战栗的瞬间。而这次的受害者,还只是个孩子。就在前一日徐太允还和这个孩子谈笑风生。他失去了理智,找出了朴兴圭,怒吼着对他拳打脚踢,逼迫对方露出真面目。就在这时,朴多曼拿来了嫌疑人的DNA检验报告,结果显示朴兴圭并非罪犯。徐太允的世界崩塌了,一切按部就班的推理竟然换来了如此的结局,他不肯相信这个结果,举枪射向了朴兴圭。
朴多曼在亲眼目睹光昊因为对警察惧怕而被火车撞死的惨状后,开始重新审视自己的人生。他辞去了警官的职务,去汉城当了推销员,过上了平静富足的生活。
2003年,他因为工作路过当年的村庄。一切似乎都未改变过,一样金黄翻涌的麦田,一样宁静的午后,不同的是当他使劲弯下腰看向沟渠深处时,再未看到女尸。朴多曼摘下了眼镜,仿佛在穿越时间望向回忆的深处。一个学生路过这里,好奇地询问朴多曼在看什么,她说前几天也有一个男人也蹲在这里看,说是想起以前在这里做过的事情。
微风吹过麦田,这个声音一直在朴多曼的记忆中沙沙作响,时间仿佛在这一刻凝固了。他忍住了眼泪,小心翼翼地询问那个男人的长相,眼神中再次掺杂了某种希望。而女孩只能告诉他,那个人就是普通的样子。
仿佛有颗石子沉重的落入朴多曼的心中,他无助地四下张望。那垂死的希望,呻吟了两声再次被践踏蹂躏直至无声哽咽。朴多曼眼含热泪望着镜头,眼中是无底的深渊。
在金基德的影片中,主角多半是哑巴或者不愿说话的人。无论是“坏小子”(Bad Guy)中暗恋女大学生的哑巴,还是“空房间”中那个一语不发喜欢潜入陌生人房间的青年,抑或是“弓”(The Bow)中几乎一片空白的台词。这样的设置都让金基德的影片有种压抑中蓄势待发的无言力量,导演在平静中寻求呐喊,就像吴宇森在静止的画面中表现速度一般精妙。正如只有白昼才能衬托黑暗的力量,只有磨难才能衬托美德的光辉,他们都用极致的对比手法展现更加强大的镜头语言。
“杀人回忆”的导演奉俊昊让镜头中的每个人都变成“盲人”,让他们在无边的黑暗中永远看不见凶手。警官找到的每条线索都看似有理,却总会在关键时刻将他们引入歧途,白忙一场。那些见过凶手的人,要不就是弱智,要不就是孩子,没人能告诉他们罪犯的相貌。那张脸就像芸芸众生中的任何一张脸,就像大海中的一滴水,无从找寻。导演运用这样无所适从的设置手法,让观众和故事中的每一个人一样陷入无法自拔的深渊,带着永不可及的绝望哀号、哭泣。这样的感觉正贴合了经历了上世纪八十年代韩国人的心理,这就不难解释为何电影一经上映便蝉联数周票房冠军,并获得多项大奖。那时候,韩国民众还在民主制的初期挣扎,在压抑中充满绝望地反抗着,看不到未来的曙光。电影中随处可见群众对政府的不满,民众在军队统治压迫下的恐惧。
导演让蒙眼的正义女神变成了瞎眼的正义女神。好人一次次倒在死亡的镰刀下,坏人却可以逍遥作案,甚至在多年后重游故地,悠然欣赏自己当年的“杰作”。
那么,是不是这个世界真的就没有正义可言了?我只能说,正义不是像好莱坞电影中好人最终取得胜利,坏人得到应有的惩罚。毕竟,正义女神没有火眼金睛,她只负责衡量和判决,捉拿罪犯不在她的职责范围内。在影片中,并没有任何一个无辜的嫌疑人冤死。就在电影末尾,徐太允警官崩溃的举枪要射杀朴兴圭的那一刻,想必很多观众不管朴兴圭是否有罪,也希望徐太允将他先杀而后快了,毕竟许久的压抑,谁都希望有个人来承担这份罪行。但是,正义女神没有让他的子弹偏差失准,每一枪都命中墙壁,也没有让飞驰的火车轧过朴兴圭的身体,他最终只是踉踉跄跄的隐入隧道的深处。
正义女神不负责追捕,只负责审判。她不能撒下天网,却清楚地知道面对嫌疑人,正义的剑该何时砍下,何时归入剑鞘。
二、奉俊昊的政治隐喻
奉俊昊之所以只拍了三部电影就可以跻身一线导演的行列,名利双收,不仅在于他纯熟的镜头语言,也因为他影片中的政治隐喻,道出了广大韩国民众的呼声。
虽然韩国已经实现了民主制,但是在他们的民族性格中,很多东西早已根深蒂固,不可扭转。例如等级分明,崇尚权威。在“不可不信缘”中,高一个年级的师兄就可以命令、呵斥甚至抡起木棍毒打学弟,无论谁称呼比自己年龄大的人都要用敬语。在“杀人回忆”中,警官问话审讯的时候,没有一个人敢质疑反抗,都是老老实实地挨骂受训。这是韩国人民族性格中不可磨灭的东西,也是造成他们压抑痛苦的根源。这种矛盾的痛苦在奉俊昊的电影中体现的尤为明显。
电影中有一个细节:白光昊被拷打的间歇,和朴多曼、乔勇谷警官一起吃饭,观看颂扬警察神勇破案的电视剧。白光昊兴奋的大叫,说这个电视节目是自己最喜欢看的,要给爸爸打电话告诉他。乔勇谷好脾气的劝他不要那么多话,好好吃饭。三个人之间的气氛简直可以用诡异的其乐融融来形容,谁能想象刚才其中一个人还在遭受毒打?警察这个角色在“杀人回忆”中代表的正是一种强权,这种强权的压力往往来自韩国政府。民众一方面觉得政府像警察对罪犯私刑拷打一样剥夺民众的人权,另一方面又景仰这种强权,感觉受到保护,就像白光昊喜欢看那个有关警察的电视剧一样。不光是韩国人,很多人都有这种对强权的依赖,也许这是人们的惰性和奴性使然,中国人不是有句古话么,“背靠大树好乘凉”,正是应证了这一说法。人的力量太渺小了,总希望依靠强大的力量寻求保护。
在故事中,警官对案件的查询仿佛总会受到来自群众的阻挠。比如,徐太允打电话询问电台点歌者的地址,他们却认为这是一个恶作剧挂断了电话;朴多曼依照自己的断定,去澡堂查询男子的下体,遭到了澡堂老板的嘲笑;警官在勘查犯罪现场的时候,经常会被破坏现场的群众打乱阵脚。警察抓罪犯是为了民众的出行安全,却得不到民众的支持,反而可以看到每次抓到一个嫌疑人,都会有大批的群众在警察局门口示威游行,抗议警察铐打嫌疑人或者咒骂他们低能的抓错了人。这充分体现了民众对政府的怀疑,有些怀疑是有根有据的,有些怀疑却是毫无来由的。正是这种互相的不信任,导致了罪犯最终逍遥法外,使得受害人死不瞑目。
高级警察徐太允的出现仿佛和当地保守落后的气氛不符合,他就像一剂强心针,给警队注入了全新的思考模式和活力。他和朴多曼,分别代表着韩国想要革新的一派和仍旧落后守旧的一派。他们一个相信理智断案,一个相信感觉。但随着事情的发展,两人的心理也逐渐发生了变化:朴多曼亲眼见到白光昊因为惧怕警察而惨死,开始反思自己的断案方式,反思自己一直以来心安理得奉行的原则是否正确?而徐太允从一开始的志得意满,到后来发现自己的一切努力都是白费,熟识的女孩在一夜之间就变成了地上冰冷的女尸。他的世界观全盘崩溃,他发现与其一步步照章办事,有理有据,不如一枪崩了那个坏蛋来得简单解恨,如果早就这么办,女孩也许就不会死了。就算当证据又一次告诉他,他的推测是错误的,他宁愿相信DNA的检验结果是错的,也不愿意再相信这个疯狂的世界有什么理智可言了。徐太允和朴多曼两人的遭遇和感情变迁,也从某方面影射了韩国当时两派势力的斗争。他们都坚信自己可以让国家更加和谐繁荣,而在斗争辩论的过程中,他们又都变得迷茫,不再坚持初衷,对现实妥协。
除了朴多曼和徐太允警官,电影中还有一个引人注目的警察乔勇谷。他擅长各种飞踹和拷打罪犯方式,每当朴多曼不想问下去了,就挥一挥手示意,乔勇谷就会义无反顾地扑上去把对方踢倒,一顿暴打。这个人物虽然暴力,但也有他正直的一面,比如他对工作兢兢业业,追逐疑犯的时候锲而不舍,受伤的时候也不大呼小叫,只是冷静的把钉子从腿上拔出来。这些其实都是值得赞许的军人精神,也是当时军政府统治值得称赞的一面。但是,事态的演变就好比那段因扎上生锈钉子而需要截肢的右腿,当他的做法不再符合现实世界的发展,就要忍痛割去,才能继续存活。这就是韩国需要废除军人统治才能继续更好发展的最终结果。
电影中还有很多诸如此类值得玩味的细节。比如伫立在稻田边那个穿红衣的稻草人。稻草人本来是用来吓唬偷食谷稻的小鸟的,人们让它穿上罪犯喜欢的红色衬衣,正是想借此转移罪犯的注意力。但是,谁都知道这是掩耳盗铃的做法,毫无用处,只能给自己几分心理安慰。也从另一个侧面,显示了社会的动荡不安,人们无力改变这一切,只好把希望托付给一个毫无用处的稻草人。
三、祈祷还是反抗?
“杀人回忆”中那个残暴聪明的杀人犯就像一种不可预知的强大力量,每个人面对他最终都会手足失措,毫无还击的余地。人们只能眼睁睁的看着他躲在墓地的后面,偷偷窃笑。这是人们对某种未知力量的恐惧,对那种浓郁浑浊的黑暗充满恐惧。
在奈特•沙马兰导演的“天兆”(Signs)中,当麦田圈大面积的出现在世界各个角落时,人们只能瞪着眼睛,守着电视,看着外星人的飞船一片片占据了天空,尖叫着四处奔逃。面对如此前所未有的景象,人们纷纷聚集在教会、教堂、寺庙,电视上的主持人也只能祈祷“愿上帝与我们同在”。
而在另一部韩国影片“奥罗拉公主”中,导演则持有不同的态度。严贞花扮演的郑顺贞看似是一名敬业努力的汽车销售员,实际上是为死去的女儿复仇的战士,她心中的痛苦像条毒蛇每天啃噬她的心,让她心中的怒火越烧越旺。郑顺贞的女儿一年前被一个恋童癖男人奸杀之后,当作垃圾一样丢到了垃圾场。而那个该千刀万剐的男人竟然在律师的庇护下,辩解自己神经失常,逃离了法律的制裁。郑顺贞的丈夫吴警官虽然身为警察,却只能坐视罪犯玩弄法律于股掌。面对无法挽回的事实,他选择平静祈祷,立志去做一个牧师。
郑顺贞精心策划,让每一个造成女儿悲惨下场的人都不得好死。而那几个人都代表了平日社会里一种不公平的现象,郑顺贞就以复仇女神的名义将他们一个个铲平。眼见妻子豁出性命为女儿奋不顾身,血流成河,撕心裂肺的哀号,吴警官就像一个醉酒的人挨了一闷棍猛醒过来,辞去了警察的工作,继续妻子未完成的复仇。
前共和党发言人纽特•格林威治在评价“星球大战”的时候,曾说过,“站在正确一方的弱者打败了站在错误一方的强者,这是一种根深蒂固的美国神话”,换言之就是胜利永远属于正义的一方。不过,对于大多数人来说,很难想象自己是那个击败大人物的英雄,毕竟那些都是小说和电影中塑造的英雄形象,而诞生的英雄数量在历史中,肯定要远远少于死于邪恶魔爪下的人,更多冲锋陷阵的人都是充当了寂寂无名炮灰。所以,绝对的说,面对危机我们该祈祷还是反抗都是缺乏说服力的。
我不能说“奥罗拉公主”中郑顺贞的做法是正确的。作为一个母亲,她是值得人尊敬敬畏的,但是作为一个人,她没有权利决定他人的生死,更何况她杀的一些人实际上罪不至死。我想,导演更多的还是想表现对社会不公平现象的不满。
能被大多数人理解并接受的观念,还是“世界大战”(War of the Worlds)中那个汤姆•克鲁斯所饰演的码头工人雷•费瑞尔形象。费瑞尔年纪轻轻就有了两个孩子,离过一次婚,但这并没有增加他责任心,他仍旧整天游手好闲,追求物质上的享受。当外星人来袭,他只得抱着女儿,领着儿子开始他们的逃亡生涯。在这中间,他们经历了争吵和信任危机,儿子离开了他去反抗外星人,他则孤注一掷的守着女儿,在一次又一次的生死关头,费瑞尔心中对女儿的责任感被唤醒。为了女儿,他杀死了那个精神失常险些暴露他们的人;在外星人抓走女儿后,急中生智的捡起地上的手榴弹塞进外星人的内核。在外人看来,这是英雄事迹,而对他来说,他只是为了保护女儿。
战胜邪恶这个信念对于大多数人来说,固然理想远大但是遥不可及,但是守护家人是很多人都会去做,而且常常会因此创造奇迹。
在“杀人回忆”中,朴多曼夸耀自己的眼光犀利,能分辨出罪犯时,局长曾经问他,有一个强奸未遂的男人和受害者的哥哥都在写笔供,让他看到底哪个人是罪犯。导演并未让朴多曼作出判断,就像那个无法结案的连环杀人案件。
有些真相会被时间的车轮碾过,被历史的风沙掩埋,人们能做的不是去追究无谓的结果。很多事情冥冥之中自有定数,就像“天兆”中,儿子的哮喘、女孩的洁癖还有母亲的去世都预示着未来发生的事情,很多结果不是我们很快就能看到的。我们能做的,就像那个保护女儿的父亲那样尽力而为,看看生活给我们怎样的答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