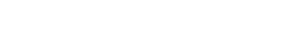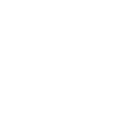中产阶级为什么比农民更买不起房
高房价、买房贵和住房难,是近六亿中国城镇居民公认的民生难题。但在不久前,建设部的一位副部长大人在一次新闻发布会上, 对这数亿市民倍感痛苦的“头等难题”所作的“典型性”的“官方诠释”,却引起了民众的“强烈反响”。按照这位副部长的说法,现在“多数居民的住房条件得到了较大改善”,真正出现“住房还比较困难”的,仅仅只是“部分城市低收入家庭”。因此,只有这些极少数人才是“住房新政”关注的“重点”。
这里一个关键的问题,就是在中国城镇居民的住房水平连“全面小康”标准(人均35平方米)一半的水平都未达到、连建设部官员自己都承认七成以上的市民还买不起房、四成左右的城市居民还是“无房户”的情况下,“住房困难”究竟是一种普遍现象,还仅仅是“部分城市低收入家庭”的“特殊现象”!把高房价和住房困难视为“新三座大山”,是公众的“真情实感”还是一种“无病呻吟”!在房地产铁三角所谓的“只是部分低收入者才有住房困难”的背后,究竟隐藏着什么样的“别有用心”?
农民比中产更能买得起房引出的话题:
究竟谁才是高房价下的“住房上的低收入者”?
既然最新一轮的“房改新政”定位于解决低收入者的住房困难,这里就提出一个问题:究竟谁才是中国城市住房上的“低收入者”,他们在城市人口中的比例究竟有多少?还有一个更重要的问题,就是在现在的高房价下,住房上需要解决困难的“低收入者”和社会阶层分析上的低收入者是不是一回事,这些基本的问题不解决,解决低收入者的住房问题,就无从谈起。
对于前面一个问题,人民日报在解读24号文件(“关于解决城市低收入家庭住房困难的若干意见”)时曾经有一个极为明确的说法。这就是“据建设部测算,目前全国仍有人均建筑面积 10平方米 以下的低收入住房困难家庭近1000万户,占城镇家庭总户数的5.5%”。而24号文件提出的“十一五”期末“廉租住房制度保障范围要扩大到低收入住房困难家庭”,也就是“全面覆盖这1000万户家庭”。也就是说,在“官方认定”中,全国城镇只有5%多的家庭属于“低收入住房困难家庭”。这与目前公认的城市中七八成人买不起房或改善不了住房条件的“说法”,正好形成了截然不同的鲜明对照;
对于第二个问题,也就是“谁是中国房地产市场上的‘低收入者’”,“房改新政”的设计者们似乎根本就没有考虑。但早在24文件出台之前的“听取意见”阶段,笔者就应邀专程赴北京,在一个“有一定级别”的、“房改新政”决策前的“内部研讨会”上,对此进行了明确的阐述。
我认为,在当时占据“相当位置”的“主流思维”中,把住房市场上的低收入者和社会阶层统计分析上的低收入者画上等号,不仅是一种理论上的片面和机械,而且也犯了方向性的错误。
实际上,住房上的“低收入者”,是一个相对房价高低的一个比较概念,有什么样的住房政治导向,有什么样的房价构成,就有什么样的“住房低收入群体”。
众所周知,在中国的社会中,最大的“低收入者”和“中低收入者”群体不是在城市,而是在农村。根据国家统计局的年度统计公报,2006年全国“全年农村居民人均纯收入3587元”,而同期全国“城镇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11759元”,城镇居民的人均可支配收入比农村居民高出2倍多(城乡之比高达3.28:1)。但是,为什么比“城里人”要“穷得多”的中国农民,从来就没有抱怨和提出过“住房问题”呢?这是因为他们解决住房问题的成本很低,房价低到让城市居民难以想象的地步。
这里,我们也以国家统计局的数据,来说明中国的城乡房价之差究竟大到了什么程度。根据国家统计局的统计年鉴, 2005年我国农村竣工的农民住宅建筑面积为62292.4万平方米(约为6.23亿),住宅竣工房屋的平均造价每平方米334.4元,这就是农民的建房成本。而同年在全国城镇销售的49587.83万平方米(约为4.96亿)商品住房,平均价格为每平方米为2937元(实际上中国绝大多数大中城市的房价,要远远超过这一“统计数据”)。也就是说,中国城镇居民的房价及解决住房问题的成本,要比中国农村居民自己建房解决住房问题的成本和代价,按照“包装”后的“官方统计”,高出了将近8倍,城镇和农村的房价之比高达8.78:1(实际情况比“官方统计”还要高得多)。
按照2005年的统计,如果城乡家庭都是以户均3口来计算的话,那么中国的农民拥有一套90平方米的住房的成本代价仅仅只需30096万元,他们的房价收入比也只有2.79。也就是说,中国农民只需用3年不到的家庭收入即可换来一套90平方米的住宅;但对中国的市民来说,他们要拥有一套90平方米的住房,则至少要掏出264330元的“真金白银”,城市居民的房价收入比为7.49(笔者注:由于在房价和收入统计上双重的“官方影响”,再加上中国城市社会中极为严重的两极分化,城镇多数居民的实际收入及“中位数水平”,要远低于官方的“平均水平”;城镇居民房价收入比的中位数,也要比官方的这个数字高得多,有些大城市市区房甚至高达20以上)。
由此不难看出,尽管城镇居民的人均可支配收入要比农村居民高2倍多,但他们在买房上的成本支出,却比农民要高出近8倍,量化住房负担的房价收入比也比农民高出数倍。这也是为什么作为中国最大的低收入群体的农民,从来没有出现过什么“住房问题”原因所在。可以说在全世界的任何地方,像中国农民这样房价收入比控制在3以内的情况,都可谓是取得了住房上“幸福指数”的高分(尽管中国农民的住宅质量还有极大的提高空间)。由此不难看出,在不同的房价体系面前,社会阶层分析中的“低收入者”,并不等于就是住房上的“低收入者”;一般意义上的“中等收入者”,也并不等于就不是住房上的“困难人群”。恰恰相反,在中国的现实社会中,在不同的住房政策和房价体系下,这两者的位置不仅经常不等同,而且有时正好相反。
所以,尽管中国农民的收入比市民的收入要低得多,但由于城乡房价的差距要比收入的差价高出数倍,更何况城镇居民的买房支出,已经占到了一般家庭一辈子收入和总财产的四分之三左右,这就造成在当今中国,社会阶层分析中的“低收入群体”,并不一定是住房上的“低收入者”;反而是城市中无人管无人问的“房改新政弃儿”——被视为“基本小康”的城市的普通民众、甚至是“中产阶级”,成了身受“新三座大山”压迫最深的“住房上的低收入者”。类似的例子在我国房价较低的小城市和西部城市也可以找到。虽然那儿城镇居民的收入要比东部和经济发达大城市低得多,但由于房价更低,使得住房问题很少像发达的大中城市和东部地区那样,成为极为突出的社会问题。
高房价下,多少人成为真正的“住房上的低收入者”
从以上的论述中人们懂得,由一系列不当的住房政策所导致的高房价,在当今社会已经成为一种实实在在的“逆向二次分配”。它使那些看起来已经步入“小康”的普通城市居民甚至是“中间阶层”,流血流汗换来的“较高收入”成了“过手财富”,变成了高房价下开发商暴富的“供品”。为了基本生存所必须的居住条件,他们不是成了“房奴”或“负翁”,就是成为“寄人篱下”的“群租者”。而在世界上各种人权宪章和居住福利中,拥有体面的居住条件,是现代人一项基本的人权和福利。
由此不难看出,在现在城乡住房上的“二元体系”和城市中多种住房供应制度实际并存的情况下(如拿着高薪的官员阶层,还可以享受获取超低价“买房”的“福利”和特权),不能把住房方面的“低收入者”人群,等同于社会阶层分析上的“低收入者”,在政策的制定中更不能把两者当作同一概念。实际上,住房上的“低收入者”,是由房价的高低来决定,而不能依据表面的收入来判断,它有着自身的特殊性和相对性。如:在北京上海等大城市,户均收入在15万元以上的家庭,在所有的统计分析中,他们可能都会被排在“中高收入者”群体之中。但是,他们的这些“中高收入”在每平方米一两万的“普通住房”的高房价面前,他们“荷包”的“含金量”就大大缩水,就只能是“低收入者”,这就是房价高低决定收入水平的特殊性所在。从某个方面来说,开发商大佬们的话也有他的“特别的道理”,这就是“中国买不起房的都是穷人”,也就是“低收入者”。
那么,如何如何衡量和界定“住房上的低收入者”呢?笔者认为,最主要的一个指标,就是要看他的收入是否可以买得起生活和工作地的住房;买房的负担,是否可控制在国际惯例的房价收入比3—6的范围内(这里还没有讲社会主义土地公有制的优越性)。具体到量化指标上,我认为,只要房价收入比超过公认的 “国际房价最难承受地区”7的水平(以7.5为界,相当于在3口之家90平方米 的住房标准下,家庭的每月的收入还达不到当地的平均房价,买不起房一平方米住房),都应该算作为“住房上的低收入群体”。
把住房上和社会统计上的“低收入者”分开,目的就是我们在制定下一步的住房政策时,可以实事求是的抓住住房方面矛盾的主要方面,“对症下药”,真正的解决广大市民普遍遇到的住房上的问题,而不是让某些房地产的“铁三角”,为了其自身的利益“屁股指挥脑袋”,故意“避重就轻”,在大搞政绩秀的同时,处心积虑去维护利益集团的特殊利益。
在当今中国,一个公认的事实是买不起房或改善不了住房条件的市民,已占到了城市人口的七八成。也就是说,中国城市“住房上的低收入者”高达70—80%;而在社会阶层的统计分析上的,城市社会的低收入者,一般在10%。所以,中国的房地产政策和调控措施,要解决“住房上的低收入者”问题,应该解决的是这70—80%人的问题,而不少在10%、甚至只有5%(如廉租房供应对象)上作秀。
众所周知,暴利和高房价是住房上“低收入阶层”的制造者。但人们应该再进一步追究的是,究竟又是谁,提供了什么样的政策和条件,给房地产市场的暴利横行和开发商肆意攫取公众财富,“提供良好的环境和氛围”的呢?是房地产铁三角利益集团操控的右倾化住房政治导向,才使开发商成为人民最大利益所在——土地权益的真正的主宰者和使用权的垄断暴利者。住房上的“低收入群体”和社会阶层统计分析上的“低收入者”两者之间为什么有那么大的差别,就在于导致高房价出现的一系列的政策和行政,实际上已经起到一个反向的“二次分配”的调节功能,它使富者越富,穷者越穷。不当住房和房地产政策导向的负面效应正在不断放大,使得逆向二次分配调节功能开始颠覆改革的成果,中间阶层成为财富被攫取和剥削的主要对象,贫富差距和两极分化正在日益拉大。
正是在高房价的盘剥下,公众的财富被“重新洗牌”:已经“全面小康”的社会中间阶层重新变为“低收入者”,重新成为 “负翁阶层”和新的“赤贫阶层”。这种极为严重的社会问题的存在,就在于高房价实际已经起到一个一个反向的社会调节作用,这也是现今的住房政策和房地产行政导向直接作用的结果。说到底,这也是对社会稳定和谐的一场大的摧残、大的浩劫。因为对任何一个社会来说,中间阶层都是社会稳定的基石。
“住房主要矛盾论战”背后的博弈:该不该动开发商暴利的蛋糕
其实,早在这一轮所谓的“房改新政”出台的数月之前,社会上的有识之士就不断通过各种媒体和场合,突出强调一个基本事实,即在城市居民中买不起房或改善不了住房条件、难以实现住房小康的人口比例,已高达中国城镇总人口的八成左右。同时还特别强调指出:“当前房地产市场的主要问题及矛盾,已经从最低和低收入者解决不了住房问题,演绎成大多数普通市民买不起房。”。
实际上,建设部的高官“把廉租住房作为建设部今年在房地产方面最重要的工作”,作为“解决老百姓反映最强烈的住房问题上的开出的‘处方’”,不仅回避了当前中国城市住房问题的主要矛盾——普通市民买不起房,而且还和温家宝总理在今年两会上政府工作报告中的有关房地产方面的论述,形成了截然相反的对比。温家宝在报告中提出:“房地产业应重点发展面向广大群众的普通商品住房”。但建设部的“工作重点”显然躲开了这个对“广大群众”的“面向”,只是把“部门作为”的目标放在了仅仅是占人口5%的“最低收入”人群。
而建设部等有关部门之所以不“重点发展面向广大群众”、收入比合适的商品房,有着其“特别的利益取向”——关键就是怕动了开发商特殊利益集团的“蛋糕”。如果建设部住房上“工作的主要目标”调整为“重点发展面向广大群众”、房价收入比控制在合理水平的住房生产供应,就势必要动开发商操控的房地产市场高价、垄断、暴利的“蛋糕”。这是开发商所最不愿意见到的。因为根据“让老百姓买得起房”这个大目标,就必须充分放开主管部门在房地产市场的种种“明文”的“隐形”的限制,允许包括自建房、经济适用房、单位建房、国家建房等各种“非盈利的开发模式”进入房地产市场,打造中低价商品住房。这就使房地产再也不能成为开发商垄断独有的“暴富制造器”。其实,那种为了开发商特殊集团的利益,回避当前住房问题的主要矛盾,避重就轻搞一些“空调”式的“调控”,实属“祸国殃民”。
这里引出了问题的核心和关键,就是当开发商操控的暴利高房价,已经空前荒唐的达到世界公认的“国际房价最难承受地区”(房价收入比为7)的数倍,社会主义中国的开发商,已成为攫取和侵害近六亿中国城市居民最大财富和利益的“寡头垄断剥削者”时,“以民为本”的执政者,制定和实施新的“房改新政”时,还是否敢于为了数亿人民的最大利益,拿几万名“开发商特殊利益者”开刀。虽然开发商操控的新一轮房价“无拘无束”的暴涨和“白纸黑字的最新文件”,再一次以事实给了人们最有说服力的“反面回答”,但人们依旧憧憬:在“全面把握‘人民群众的新期待’十*大”后,执政者在住房——这个普通民众的最大利益面,推出“适应时代要求和人民愿望”的全新的“行动纲领和大政方针”。
高房价、买房贵和住房难,是近六亿中国城镇居民公认的民生难题。但在不久前,建设部的一位副部长大人在一次新闻发布会上, 对这数亿市民倍感痛苦的“头等难题”所作的“典型性”的“官方诠释”,却引起了民众的“强烈反响”。按照这位副部长的说法,现在“多数居民的住房条件得到了较大改善”,真正出现“住房还比较困难”的,仅仅只是“部分城市低收入家庭”。因此,只有这些极少数人才是“住房新政”关注的“重点”。
这里一个关键的问题,就是在中国城镇居民的住房水平连“全面小康”标准(人均35平方米)一半的水平都未达到、连建设部官员自己都承认七成以上的市民还买不起房、四成左右的城市居民还是“无房户”的情况下,“住房困难”究竟是一种普遍现象,还仅仅是“部分城市低收入家庭”的“特殊现象”!把高房价和住房困难视为“新三座大山”,是公众的“真情实感”还是一种“无病呻吟”!在房地产铁三角所谓的“只是部分低收入者才有住房困难”的背后,究竟隐藏着什么样的“别有用心”?
农民比中产更能买得起房引出的话题:
究竟谁才是高房价下的“住房上的低收入者”?
既然最新一轮的“房改新政”定位于解决低收入者的住房困难,这里就提出一个问题:究竟谁才是中国城市住房上的“低收入者”,他们在城市人口中的比例究竟有多少?还有一个更重要的问题,就是在现在的高房价下,住房上需要解决困难的“低收入者”和社会阶层分析上的低收入者是不是一回事,这些基本的问题不解决,解决低收入者的住房问题,就无从谈起。
对于前面一个问题,人民日报在解读24号文件(“关于解决城市低收入家庭住房困难的若干意见”)时曾经有一个极为明确的说法。这就是“据建设部测算,目前全国仍有人均建筑面积 10平方米 以下的低收入住房困难家庭近1000万户,占城镇家庭总户数的5.5%”。而24号文件提出的“十一五”期末“廉租住房制度保障范围要扩大到低收入住房困难家庭”,也就是“全面覆盖这1000万户家庭”。也就是说,在“官方认定”中,全国城镇只有5%多的家庭属于“低收入住房困难家庭”。这与目前公认的城市中七八成人买不起房或改善不了住房条件的“说法”,正好形成了截然不同的鲜明对照;
对于第二个问题,也就是“谁是中国房地产市场上的‘低收入者’”,“房改新政”的设计者们似乎根本就没有考虑。但早在24文件出台之前的“听取意见”阶段,笔者就应邀专程赴北京,在一个“有一定级别”的、“房改新政”决策前的“内部研讨会”上,对此进行了明确的阐述。
我认为,在当时占据“相当位置”的“主流思维”中,把住房市场上的低收入者和社会阶层统计分析上的低收入者画上等号,不仅是一种理论上的片面和机械,而且也犯了方向性的错误。
实际上,住房上的“低收入者”,是一个相对房价高低的一个比较概念,有什么样的住房政治导向,有什么样的房价构成,就有什么样的“住房低收入群体”。
众所周知,在中国的社会中,最大的“低收入者”和“中低收入者”群体不是在城市,而是在农村。根据国家统计局的年度统计公报,2006年全国“全年农村居民人均纯收入3587元”,而同期全国“城镇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11759元”,城镇居民的人均可支配收入比农村居民高出2倍多(城乡之比高达3.28:1)。但是,为什么比“城里人”要“穷得多”的中国农民,从来就没有抱怨和提出过“住房问题”呢?这是因为他们解决住房问题的成本很低,房价低到让城市居民难以想象的地步。
这里,我们也以国家统计局的数据,来说明中国的城乡房价之差究竟大到了什么程度。根据国家统计局的统计年鉴, 2005年我国农村竣工的农民住宅建筑面积为62292.4万平方米(约为6.23亿),住宅竣工房屋的平均造价每平方米334.4元,这就是农民的建房成本。而同年在全国城镇销售的49587.83万平方米(约为4.96亿)商品住房,平均价格为每平方米为2937元(实际上中国绝大多数大中城市的房价,要远远超过这一“统计数据”)。也就是说,中国城镇居民的房价及解决住房问题的成本,要比中国农村居民自己建房解决住房问题的成本和代价,按照“包装”后的“官方统计”,高出了将近8倍,城镇和农村的房价之比高达8.78:1(实际情况比“官方统计”还要高得多)。
按照2005年的统计,如果城乡家庭都是以户均3口来计算的话,那么中国的农民拥有一套90平方米的住房的成本代价仅仅只需30096万元,他们的房价收入比也只有2.79。也就是说,中国农民只需用3年不到的家庭收入即可换来一套90平方米的住宅;但对中国的市民来说,他们要拥有一套90平方米的住房,则至少要掏出264330元的“真金白银”,城市居民的房价收入比为7.49(笔者注:由于在房价和收入统计上双重的“官方影响”,再加上中国城市社会中极为严重的两极分化,城镇多数居民的实际收入及“中位数水平”,要远低于官方的“平均水平”;城镇居民房价收入比的中位数,也要比官方的这个数字高得多,有些大城市市区房甚至高达20以上)。
由此不难看出,尽管城镇居民的人均可支配收入要比农村居民高2倍多,但他们在买房上的成本支出,却比农民要高出近8倍,量化住房负担的房价收入比也比农民高出数倍。这也是为什么作为中国最大的低收入群体的农民,从来没有出现过什么“住房问题”原因所在。可以说在全世界的任何地方,像中国农民这样房价收入比控制在3以内的情况,都可谓是取得了住房上“幸福指数”的高分(尽管中国农民的住宅质量还有极大的提高空间)。由此不难看出,在不同的房价体系面前,社会阶层分析中的“低收入者”,并不等于就是住房上的“低收入者”;一般意义上的“中等收入者”,也并不等于就不是住房上的“困难人群”。恰恰相反,在中国的现实社会中,在不同的住房政策和房价体系下,这两者的位置不仅经常不等同,而且有时正好相反。
所以,尽管中国农民的收入比市民的收入要低得多,但由于城乡房价的差距要比收入的差价高出数倍,更何况城镇居民的买房支出,已经占到了一般家庭一辈子收入和总财产的四分之三左右,这就造成在当今中国,社会阶层分析中的“低收入群体”,并不一定是住房上的“低收入者”;反而是城市中无人管无人问的“房改新政弃儿”——被视为“基本小康”的城市的普通民众、甚至是“中产阶级”,成了身受“新三座大山”压迫最深的“住房上的低收入者”。类似的例子在我国房价较低的小城市和西部城市也可以找到。虽然那儿城镇居民的收入要比东部和经济发达大城市低得多,但由于房价更低,使得住房问题很少像发达的大中城市和东部地区那样,成为极为突出的社会问题。
高房价下,多少人成为真正的“住房上的低收入者”
从以上的论述中人们懂得,由一系列不当的住房政策所导致的高房价,在当今社会已经成为一种实实在在的“逆向二次分配”。它使那些看起来已经步入“小康”的普通城市居民甚至是“中间阶层”,流血流汗换来的“较高收入”成了“过手财富”,变成了高房价下开发商暴富的“供品”。为了基本生存所必须的居住条件,他们不是成了“房奴”或“负翁”,就是成为“寄人篱下”的“群租者”。而在世界上各种人权宪章和居住福利中,拥有体面的居住条件,是现代人一项基本的人权和福利。
由此不难看出,在现在城乡住房上的“二元体系”和城市中多种住房供应制度实际并存的情况下(如拿着高薪的官员阶层,还可以享受获取超低价“买房”的“福利”和特权),不能把住房方面的“低收入者”人群,等同于社会阶层分析上的“低收入者”,在政策的制定中更不能把两者当作同一概念。实际上,住房上的“低收入者”,是由房价的高低来决定,而不能依据表面的收入来判断,它有着自身的特殊性和相对性。如:在北京上海等大城市,户均收入在15万元以上的家庭,在所有的统计分析中,他们可能都会被排在“中高收入者”群体之中。但是,他们的这些“中高收入”在每平方米一两万的“普通住房”的高房价面前,他们“荷包”的“含金量”就大大缩水,就只能是“低收入者”,这就是房价高低决定收入水平的特殊性所在。从某个方面来说,开发商大佬们的话也有他的“特别的道理”,这就是“中国买不起房的都是穷人”,也就是“低收入者”。
那么,如何如何衡量和界定“住房上的低收入者”呢?笔者认为,最主要的一个指标,就是要看他的收入是否可以买得起生活和工作地的住房;买房的负担,是否可控制在国际惯例的房价收入比3—6的范围内(这里还没有讲社会主义土地公有制的优越性)。具体到量化指标上,我认为,只要房价收入比超过公认的 “国际房价最难承受地区”7的水平(以7.5为界,相当于在3口之家90平方米 的住房标准下,家庭的每月的收入还达不到当地的平均房价,买不起房一平方米住房),都应该算作为“住房上的低收入群体”。
把住房上和社会统计上的“低收入者”分开,目的就是我们在制定下一步的住房政策时,可以实事求是的抓住住房方面矛盾的主要方面,“对症下药”,真正的解决广大市民普遍遇到的住房上的问题,而不是让某些房地产的“铁三角”,为了其自身的利益“屁股指挥脑袋”,故意“避重就轻”,在大搞政绩秀的同时,处心积虑去维护利益集团的特殊利益。
在当今中国,一个公认的事实是买不起房或改善不了住房条件的市民,已占到了城市人口的七八成。也就是说,中国城市“住房上的低收入者”高达70—80%;而在社会阶层的统计分析上的,城市社会的低收入者,一般在10%。所以,中国的房地产政策和调控措施,要解决“住房上的低收入者”问题,应该解决的是这70—80%人的问题,而不少在10%、甚至只有5%(如廉租房供应对象)上作秀。
众所周知,暴利和高房价是住房上“低收入阶层”的制造者。但人们应该再进一步追究的是,究竟又是谁,提供了什么样的政策和条件,给房地产市场的暴利横行和开发商肆意攫取公众财富,“提供良好的环境和氛围”的呢?是房地产铁三角利益集团操控的右倾化住房政治导向,才使开发商成为人民最大利益所在——土地权益的真正的主宰者和使用权的垄断暴利者。住房上的“低收入群体”和社会阶层统计分析上的“低收入者”两者之间为什么有那么大的差别,就在于导致高房价出现的一系列的政策和行政,实际上已经起到一个反向的“二次分配”的调节功能,它使富者越富,穷者越穷。不当住房和房地产政策导向的负面效应正在不断放大,使得逆向二次分配调节功能开始颠覆改革的成果,中间阶层成为财富被攫取和剥削的主要对象,贫富差距和两极分化正在日益拉大。
正是在高房价的盘剥下,公众的财富被“重新洗牌”:已经“全面小康”的社会中间阶层重新变为“低收入者”,重新成为 “负翁阶层”和新的“赤贫阶层”。这种极为严重的社会问题的存在,就在于高房价实际已经起到一个一个反向的社会调节作用,这也是现今的住房政策和房地产行政导向直接作用的结果。说到底,这也是对社会稳定和谐的一场大的摧残、大的浩劫。因为对任何一个社会来说,中间阶层都是社会稳定的基石。
“住房主要矛盾论战”背后的博弈:该不该动开发商暴利的蛋糕
其实,早在这一轮所谓的“房改新政”出台的数月之前,社会上的有识之士就不断通过各种媒体和场合,突出强调一个基本事实,即在城市居民中买不起房或改善不了住房条件、难以实现住房小康的人口比例,已高达中国城镇总人口的八成左右。同时还特别强调指出:“当前房地产市场的主要问题及矛盾,已经从最低和低收入者解决不了住房问题,演绎成大多数普通市民买不起房。”。
实际上,建设部的高官“把廉租住房作为建设部今年在房地产方面最重要的工作”,作为“解决老百姓反映最强烈的住房问题上的开出的‘处方’”,不仅回避了当前中国城市住房问题的主要矛盾——普通市民买不起房,而且还和温家宝总理在今年两会上政府工作报告中的有关房地产方面的论述,形成了截然相反的对比。温家宝在报告中提出:“房地产业应重点发展面向广大群众的普通商品住房”。但建设部的“工作重点”显然躲开了这个对“广大群众”的“面向”,只是把“部门作为”的目标放在了仅仅是占人口5%的“最低收入”人群。
而建设部等有关部门之所以不“重点发展面向广大群众”、收入比合适的商品房,有着其“特别的利益取向”——关键就是怕动了开发商特殊利益集团的“蛋糕”。如果建设部住房上“工作的主要目标”调整为“重点发展面向广大群众”、房价收入比控制在合理水平的住房生产供应,就势必要动开发商操控的房地产市场高价、垄断、暴利的“蛋糕”。这是开发商所最不愿意见到的。因为根据“让老百姓买得起房”这个大目标,就必须充分放开主管部门在房地产市场的种种“明文”的“隐形”的限制,允许包括自建房、经济适用房、单位建房、国家建房等各种“非盈利的开发模式”进入房地产市场,打造中低价商品住房。这就使房地产再也不能成为开发商垄断独有的“暴富制造器”。其实,那种为了开发商特殊集团的利益,回避当前住房问题的主要矛盾,避重就轻搞一些“空调”式的“调控”,实属“祸国殃民”。
这里引出了问题的核心和关键,就是当开发商操控的暴利高房价,已经空前荒唐的达到世界公认的“国际房价最难承受地区”(房价收入比为7)的数倍,社会主义中国的开发商,已成为攫取和侵害近六亿中国城市居民最大财富和利益的“寡头垄断剥削者”时,“以民为本”的执政者,制定和实施新的“房改新政”时,还是否敢于为了数亿人民的最大利益,拿几万名“开发商特殊利益者”开刀。虽然开发商操控的新一轮房价“无拘无束”的暴涨和“白纸黑字的最新文件”,再一次以事实给了人们最有说服力的“反面回答”,但人们依旧憧憬:在“全面把握‘人民群众的新期待’十*大”后,执政者在住房——这个普通民众的最大利益面,推出“适应时代要求和人民愿望”的全新的“行动纲领和大政方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