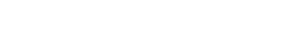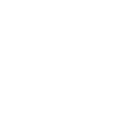关于徐静蕾的角色,未必是演技不好的问题,而是这个角色的对核心主题的作用不大,删掉她的戏份不会影响总体表达。但是,这个女人的存在毕竟增添了许多人性的东西,一个异于男人世界的美感。这个美感不必再是为他人做牺牲,也不是浓妆艳抹,而是很多人提到的,“到了最后也不知道这个女人究竟爱谁”。如果我们不是按照好莱坞通俗剧的套路,而是从身边去考察的话,或许总有这样的情况。套用洪晃的博文题:《满街都是包法利夫人》。徐静蕾的角色是原本要本送到去当“瘦马”(“你听出我的扬州话了?”还真是笑场。),她对此的态度是模糊的(现实中很多从事那种职业的人本就不背负道德包袱的,只是谋生而已),赵二虎将她抢回来,他是她的发小,如果按照通俗的道德观,还是她的恩人,但未必是她希望爱的一个人。这个女人,用现在的词来形容,是有点文艺情调的,她会期待一个有点“文化”的人,《刺马》中将之处理成对权力的欲望,实际上是很粗暴的。“包法利夫人”的要求是辛苦赚钱的丈夫还需懂情调,这当然是很难满足的。但幻想总是这样传承着,“绿窗帘”和“红窗帘”都想要。因此,抛弃演技的争论,徐静蕾的角色本身是成立的,就像太平军将领黄本身的滋味万种一样,只是她对核心主题的贡献比较少而已。陈可辛在《三联》的采访也说,“其实我没拍过女性电影,我电影里的女人都是很模糊的。……一个女人令一个男人那么痴迷,只有一个理由,那就是不知道她是谁。我都是从男人的角度去拍我希望看到的东西。”而杀死她,实际上是姜午阳代表的那种很单纯的男人式情谊对女人的误解和伤害。他那种观念会认为这两种东西是对立的,但兄弟情所遭受的威胁其实比这大得很,“兄弟乱我兄弟者,必杀之”这个戒条实际上意味着他们对兄弟情可能从内部自我破解是有预感的。《花关索传》叙刘关张桃园结义时,刘备道:“我独自一身。你二人有老小挂心,恐有回心。”关公道:“我坏了老小,共哥哥同去。”张飞道:“你怎下得手杀自家老小?哥哥杀了我家老小,我杀哥哥的老小。”刘备道:“也说得是。”可见这是脆弱而自欺欺人的。
《三联》选取“人人都是庞青云”来描述这部影片,对又不对。从人人都是命运的一枚棋子、人人又都想要掌握自己命运来说,是这样。好的故事都是原型寓言。但这里又有些特殊的东西。
这是一部饥民的历史,和奥斯维辛等著名时刻一样,它意味着人性被放诸极端的境地,生存和道德成了对立的选择。经过那个时刻的千千万万人,都曾过有过不同的选择和折磨,电影和戏剧化的故事使它通过庞青云放大了。庞青云说他从死人堆中出来的时候,他就死了,他的人性其实不是阴暗,而是灰暗。
庞青云的表演很大程度上被认为是虚伪的,他是有野心的。但抛除感情色彩,我们不妨说这是“抱负”,他代表的是为了光辉的目标、可以不择手段。这种思想朝前回溯几十年,是统治性的。庞青云在苏州城杀人,到南京城救人,在他那里有个大与小的博弈,包括利用兄弟感情来成大事。这在逻辑上初看是没有问题的。它是我们熟悉的承诺的意识形态,就是未来我们会过上好日子,所以现在要做出牺牲。这个逻辑的漏洞其实很明显,就是未来也未必过上好日子。苏州城的士兵为南京城人死了,但南京没有获得好的统治的话,那些人就是白白死掉了。这个逻辑放大了是要建设一个“理想社会”(你知道它的名字),它成为一个最高目标,理出了一个历史的道路,成为在这条路上的所有个人的价值之源。而不是个人本身的幸福作为价值之源。这样一个建构需要一个强大的统治者,虽然它会打扮成理性的面目出场。用电影里的话就是“只能有一个头。”这种思想会认为现存的社会是不道德的(所以会产生新旧的对立),那么奔向幸福的过程,就要不惜一切手段来达到他们的目的。他们认为由于其目的的道德性,在手段上不会存在不道德的问题。所以庞青云认为赵二虎应该理解他的牺牲,他认为这是历史的代价。而在自由主义看来,一个人的痛苦并不能被另一个人的快乐来抵消,任何人都不得被用来做试验品与牺牲品。此外,庞青云代表的意识会认为他们是孤独的,他的驭民术认为人民所能懂得和理解的有限,让他们知道得多反而会误事,对他们过分迁就会造成放纵。在这种情况下,感情、感性比理性更具有感召力,那就是我们是兄弟,所以你要相信我。最近有个段子,是中国一个号称“女巴菲特”的大股神劝一个股民放弃股票:这只股和你命相不合,不投缘,你还是抛了吧。这个感性号召或者说“动员”走到反面就是像《叫魂:1768年中国妖术大恐慌》显示的那样。利用感性的东西来成事,在中国可能是特别典型的。从农民起义到某某某到文革都是如此,而烦死人的民族主义狂热也是此类。
《色戒》中重庆特务头目也是为了目标可以不顾手段、不管王佳芝感受的代表,而后者的走向刺杀也是受了朦胧的爱情的鼓励。
这有点离题了,回头来说庞青云哭刘德华的死,其悲哀是真挚可信的,实际上那时候他已经枯干了,大臣们赞扬他的时候,他是沉默的,那是他的关键时刻,他赢来了做大事的机会,但他并不高兴,更大的目标到此隐身了。但最大的谜底其实也留下了,那就是如果他有机会通向最高权力(有人做到了),那么路上铺下的牺牲不说,最后的他会严格执行自己的目标吗?他会因为过程的孤独和反复的折磨而灭绝人性吗?他能承担得了构建那个“理想”的强大压力吗?他会得意于“无限风光在险峰”吗?
在波普尔看来,人类只是具有有限理性,因此不可能建立完美的社会。只有这种对限制的认识才能尽可能地减少悲剧,特别是那种为追求天堂而制造了人为的悲剧。庞青云最终以棋子的悲剧证明了他是人人之一,尚未获得“一将功成万骨枯”的机会。在这种阶段,我们才是和他有着认同的。
《三联》选取“人人都是庞青云”来描述这部影片,对又不对。从人人都是命运的一枚棋子、人人又都想要掌握自己命运来说,是这样。好的故事都是原型寓言。但这里又有些特殊的东西。
这是一部饥民的历史,和奥斯维辛等著名时刻一样,它意味着人性被放诸极端的境地,生存和道德成了对立的选择。经过那个时刻的千千万万人,都曾过有过不同的选择和折磨,电影和戏剧化的故事使它通过庞青云放大了。庞青云说他从死人堆中出来的时候,他就死了,他的人性其实不是阴暗,而是灰暗。
庞青云的表演很大程度上被认为是虚伪的,他是有野心的。但抛除感情色彩,我们不妨说这是“抱负”,他代表的是为了光辉的目标、可以不择手段。这种思想朝前回溯几十年,是统治性的。庞青云在苏州城杀人,到南京城救人,在他那里有个大与小的博弈,包括利用兄弟感情来成大事。这在逻辑上初看是没有问题的。它是我们熟悉的承诺的意识形态,就是未来我们会过上好日子,所以现在要做出牺牲。这个逻辑的漏洞其实很明显,就是未来也未必过上好日子。苏州城的士兵为南京城人死了,但南京没有获得好的统治的话,那些人就是白白死掉了。这个逻辑放大了是要建设一个“理想社会”(你知道它的名字),它成为一个最高目标,理出了一个历史的道路,成为在这条路上的所有个人的价值之源。而不是个人本身的幸福作为价值之源。这样一个建构需要一个强大的统治者,虽然它会打扮成理性的面目出场。用电影里的话就是“只能有一个头。”这种思想会认为现存的社会是不道德的(所以会产生新旧的对立),那么奔向幸福的过程,就要不惜一切手段来达到他们的目的。他们认为由于其目的的道德性,在手段上不会存在不道德的问题。所以庞青云认为赵二虎应该理解他的牺牲,他认为这是历史的代价。而在自由主义看来,一个人的痛苦并不能被另一个人的快乐来抵消,任何人都不得被用来做试验品与牺牲品。此外,庞青云代表的意识会认为他们是孤独的,他的驭民术认为人民所能懂得和理解的有限,让他们知道得多反而会误事,对他们过分迁就会造成放纵。在这种情况下,感情、感性比理性更具有感召力,那就是我们是兄弟,所以你要相信我。最近有个段子,是中国一个号称“女巴菲特”的大股神劝一个股民放弃股票:这只股和你命相不合,不投缘,你还是抛了吧。这个感性号召或者说“动员”走到反面就是像《叫魂:1768年中国妖术大恐慌》显示的那样。利用感性的东西来成事,在中国可能是特别典型的。从农民起义到某某某到文革都是如此,而烦死人的民族主义狂热也是此类。
《色戒》中重庆特务头目也是为了目标可以不顾手段、不管王佳芝感受的代表,而后者的走向刺杀也是受了朦胧的爱情的鼓励。
这有点离题了,回头来说庞青云哭刘德华的死,其悲哀是真挚可信的,实际上那时候他已经枯干了,大臣们赞扬他的时候,他是沉默的,那是他的关键时刻,他赢来了做大事的机会,但他并不高兴,更大的目标到此隐身了。但最大的谜底其实也留下了,那就是如果他有机会通向最高权力(有人做到了),那么路上铺下的牺牲不说,最后的他会严格执行自己的目标吗?他会因为过程的孤独和反复的折磨而灭绝人性吗?他能承担得了构建那个“理想”的强大压力吗?他会得意于“无限风光在险峰”吗?
在波普尔看来,人类只是具有有限理性,因此不可能建立完美的社会。只有这种对限制的认识才能尽可能地减少悲剧,特别是那种为追求天堂而制造了人为的悲剧。庞青云最终以棋子的悲剧证明了他是人人之一,尚未获得“一将功成万骨枯”的机会。在这种阶段,我们才是和他有着认同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