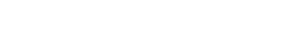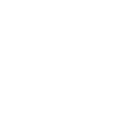1992年,我比现在年轻14岁,相应的生活态度也要积极100倍。那个时候我所有的心思都是在琢磨如何做一名招人喜欢的的好学生。当然,1992年我的老二已经学会了勃起,看到胡同里有人打架也知道躲远点别被砖拍着。除此之外,我还记得那年发生了好多奇怪的事情,可如今能够勉强回忆起来的却也只剩下一些支离破碎似是而非的声音与味道了。
大概快要到年末的时候,有一天。我的同桌突然问我知不知道TAIWAN的小虎队。还没等我回答,小虎队就已经迅速在北京所有的小学里全面扎根儿了。即便之前已经有陈百强的《一生何求》与草蜢的《家有仙妻》垫底儿,仍然是几乎一夜之间,每一所学校,每一个班级都开始有喜爱表现的男孩组建起“小狼队”“小猫队”活动。而在此之前,我个人最为欣赏的歌手与作品分别是蔡国庆和他的《北京的桥》。
我得说;在那个精神生活相对乏善可陈时候;小虎队如同川贝止咳露一样温软滋润,它的出现极大促进了北京市中小学生青春期的提前到来。简直比初恋初吻更要激荡人心。
虽然这三个人现在看起来跟傻逼一模一样。
真正毕业的时候,我认真的抄了一首《爱》送给我的同桌,我的同桌回赠了我一篇儿《青苹果乐园》。
后来与崔玮老师谈及此段,崔老师说当时不光有小虎队,周华健带着《风雨无阻》也闯进了北京。可我却总觉得周华健是上了初中以后才冒出来的。不知道是我错了,还是崔玮老师错了,抑或是周华健错了。
真正上了初中,当代歌坛已然是四大天王的天下了。间歇崔健老狼笔昂李春波杰克逊张信哲也都来搅过局,各领一时风骚。至于魔言三杰,唐朝黑豹什么的还是天外隐雷,大概要再过两年才在我的身边出现。让人记忆尤深的一首歌是《水手》,来自于TAIWAN的瘸逼郑智化。
1997年,我投考美院附中。记忆中的声音是任贤齐的《心太软》;画面是丫骑着摩托车满世界跑。我还记得到了面试的时候,大家都传考官喜欢摇滚,谁摇滚录取谁。那会儿我哪知道摇滚是谁呀!吓的赶紧向前面的哥儿们打听哪支乐队最牛逼。哥儿们说“涅磐”。于是进屋我就跟老师说除了画画我就爱听“涅磐”。老师问我那你喜欢“哪挖那”哪首歌,我说老师您听错了,我刚说的是“涅磐”,不是“哪挖那”。
灰飞烟灭。
当年另外值得一提的是;在落榜生大聚会上我的一位东北籍的同学在醉酒后声情并茂的为大家演唱了全本的《十八摸》,说实话;当时在场的所有人都裂了,关于性想问又不敢问的一切问题全都有了答案。用崔健的话说就是“象是一场风雨吹打着我的脸”。真正的醍醐灌顶。东北同学不已为然,他说去年老家过年时还把骡子唱的直撒尿呢。
失败的升学;无望的单恋。这些又算的了什么呢?!《十八摸》让我明确了毕生的追求,“哪挖那”让我了解了艺术的真谛。知耻而后勇,终于,我上了摇滚的贼船。
上个世纪末那时候北京的艺术家还不象现在这么多,玩摇滚的与听摇滚的就都已算是比较卓尔不群骇世惊俗的文化贵族了。回首当初,自己年轻气盛当仁不让。几乎只要是头发超过40厘米的主儿出的专辑就没有落下的。至于做个画家的理想,那会儿我已经觉得去琉璃厂卖打口盘比去中央美院画女人体来劲多了。
事实上,摇滚是这么个事,它在帮你释放多余荷尔蒙的同时,也或多或少的能讲述一些浅显的人生经验。举个例子;比如说美女。她们能改变你的人生观,让人对世界充满期待。但是一旦当你觉得期待的将要得到,她们又马上再去别的地方普度众生,让其他人觉得一切无限美好。这个道理何勇在《姑娘漂亮》里就曾表达过。我废物,摇滚半天,也是最近才弄明白。
后来我上了高中,3年里几乎只听“平克”与“大门”的专辑。只听他们是因为我觉得这俩乐队歌能够带给人一种制幻的体验,如坠中阴。要知道那时候在北京实在不太容易搞到毒品。我是拿CD当LSD使了。平心而论;当时的国内摇滚里面舌头和诅咒还成。而出过几期便自行夭折的《朋克时代》及其深度吹捧的盘古则是不折不扣纯粹的傻逼。
大学以后,我听的歌越来越少了,无论中国的还是外国的。偶尔放张电影原声吵吵耳朵,聊胜于无。想的起来的是HOT走了F4来了,我问肖央F4是啥;肖老师说F4是奶罩的尺寸,中国姑娘都没戏。接下来周杰伦开始长时间走红,满大街都是《双截棍》《龙卷风》。最后新疆人刀郎出了首人人都会唱的歌,叫《冲动的惩罚》。没听的时候我还当是写给未婚先孕女青年的呢。
鉴于在最后的学生时代大家都在努力学习如何招人喜欢的本领,我决定另辟蹊径炼就一身在最短的时间内最大限度招人讨厌的能耐。顺便也明确了一下自己的终极理想;是的,就是要做一个没有任何理想的人。
值得自豪的是;我的能耐炼成了,理想也实现了。
至于歌儿;彻底没有了。现在我耳朵里面的声音太多。吵的慌。
2007年,我依次患上了失眠症,干眼症,夜盲症还有可怕的图雷特氏综合症。因为这些病症对眼睛的影响,我不得不象王家卫一样在大白天带着墨镜招摇过市。我知道,我的这副操性俨然摇滚。以至于一次聚会上有个傻逼直说看过我的演出,还没完没了的问我乐队叫什么来的?我心里烦,就告诉他我的乐队叫“鸡巴”,对,没错,就是鸡巴的鸡;鸡巴的巴。
王昂
大概快要到年末的时候,有一天。我的同桌突然问我知不知道TAIWAN的小虎队。还没等我回答,小虎队就已经迅速在北京所有的小学里全面扎根儿了。即便之前已经有陈百强的《一生何求》与草蜢的《家有仙妻》垫底儿,仍然是几乎一夜之间,每一所学校,每一个班级都开始有喜爱表现的男孩组建起“小狼队”“小猫队”活动。而在此之前,我个人最为欣赏的歌手与作品分别是蔡国庆和他的《北京的桥》。
我得说;在那个精神生活相对乏善可陈时候;小虎队如同川贝止咳露一样温软滋润,它的出现极大促进了北京市中小学生青春期的提前到来。简直比初恋初吻更要激荡人心。
虽然这三个人现在看起来跟傻逼一模一样。
真正毕业的时候,我认真的抄了一首《爱》送给我的同桌,我的同桌回赠了我一篇儿《青苹果乐园》。
后来与崔玮老师谈及此段,崔老师说当时不光有小虎队,周华健带着《风雨无阻》也闯进了北京。可我却总觉得周华健是上了初中以后才冒出来的。不知道是我错了,还是崔玮老师错了,抑或是周华健错了。
真正上了初中,当代歌坛已然是四大天王的天下了。间歇崔健老狼笔昂李春波杰克逊张信哲也都来搅过局,各领一时风骚。至于魔言三杰,唐朝黑豹什么的还是天外隐雷,大概要再过两年才在我的身边出现。让人记忆尤深的一首歌是《水手》,来自于TAIWAN的瘸逼郑智化。
1997年,我投考美院附中。记忆中的声音是任贤齐的《心太软》;画面是丫骑着摩托车满世界跑。我还记得到了面试的时候,大家都传考官喜欢摇滚,谁摇滚录取谁。那会儿我哪知道摇滚是谁呀!吓的赶紧向前面的哥儿们打听哪支乐队最牛逼。哥儿们说“涅磐”。于是进屋我就跟老师说除了画画我就爱听“涅磐”。老师问我那你喜欢“哪挖那”哪首歌,我说老师您听错了,我刚说的是“涅磐”,不是“哪挖那”。
灰飞烟灭。
当年另外值得一提的是;在落榜生大聚会上我的一位东北籍的同学在醉酒后声情并茂的为大家演唱了全本的《十八摸》,说实话;当时在场的所有人都裂了,关于性想问又不敢问的一切问题全都有了答案。用崔健的话说就是“象是一场风雨吹打着我的脸”。真正的醍醐灌顶。东北同学不已为然,他说去年老家过年时还把骡子唱的直撒尿呢。
失败的升学;无望的单恋。这些又算的了什么呢?!《十八摸》让我明确了毕生的追求,“哪挖那”让我了解了艺术的真谛。知耻而后勇,终于,我上了摇滚的贼船。
上个世纪末那时候北京的艺术家还不象现在这么多,玩摇滚的与听摇滚的就都已算是比较卓尔不群骇世惊俗的文化贵族了。回首当初,自己年轻气盛当仁不让。几乎只要是头发超过40厘米的主儿出的专辑就没有落下的。至于做个画家的理想,那会儿我已经觉得去琉璃厂卖打口盘比去中央美院画女人体来劲多了。
事实上,摇滚是这么个事,它在帮你释放多余荷尔蒙的同时,也或多或少的能讲述一些浅显的人生经验。举个例子;比如说美女。她们能改变你的人生观,让人对世界充满期待。但是一旦当你觉得期待的将要得到,她们又马上再去别的地方普度众生,让其他人觉得一切无限美好。这个道理何勇在《姑娘漂亮》里就曾表达过。我废物,摇滚半天,也是最近才弄明白。
后来我上了高中,3年里几乎只听“平克”与“大门”的专辑。只听他们是因为我觉得这俩乐队歌能够带给人一种制幻的体验,如坠中阴。要知道那时候在北京实在不太容易搞到毒品。我是拿CD当LSD使了。平心而论;当时的国内摇滚里面舌头和诅咒还成。而出过几期便自行夭折的《朋克时代》及其深度吹捧的盘古则是不折不扣纯粹的傻逼。
大学以后,我听的歌越来越少了,无论中国的还是外国的。偶尔放张电影原声吵吵耳朵,聊胜于无。想的起来的是HOT走了F4来了,我问肖央F4是啥;肖老师说F4是奶罩的尺寸,中国姑娘都没戏。接下来周杰伦开始长时间走红,满大街都是《双截棍》《龙卷风》。最后新疆人刀郎出了首人人都会唱的歌,叫《冲动的惩罚》。没听的时候我还当是写给未婚先孕女青年的呢。
鉴于在最后的学生时代大家都在努力学习如何招人喜欢的本领,我决定另辟蹊径炼就一身在最短的时间内最大限度招人讨厌的能耐。顺便也明确了一下自己的终极理想;是的,就是要做一个没有任何理想的人。
值得自豪的是;我的能耐炼成了,理想也实现了。
至于歌儿;彻底没有了。现在我耳朵里面的声音太多。吵的慌。
2007年,我依次患上了失眠症,干眼症,夜盲症还有可怕的图雷特氏综合症。因为这些病症对眼睛的影响,我不得不象王家卫一样在大白天带着墨镜招摇过市。我知道,我的这副操性俨然摇滚。以至于一次聚会上有个傻逼直说看过我的演出,还没完没了的问我乐队叫什么来的?我心里烦,就告诉他我的乐队叫“鸡巴”,对,没错,就是鸡巴的鸡;鸡巴的巴。
王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