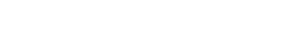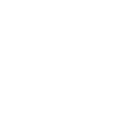《母亲》是继1974年的《寅次郎的故事——爱情和伴侣》之后,吉永小百合和山田洋次的再度携手,这一次山田洋次借吉永小百合为坚忍顽强的日本女性一洒同情之泪。

影片《母亲》海报
故事主要集中在1940~1941,日本发动太平洋战争时期,日本国内全民动员发动“圣战”,全面入侵亚洲,作为故事主角的母亲的丈夫,父亲,因发表反对军国主义的言论被投进监狱,母亲本为富裕的警察局长之女,警察局长早年不满女儿嫁给穷知识分子,又嫌女婿是个“叛徒”与女儿脱离关系。此时日本国内生活日益困苦,母亲一边每天去看守所(后来是监狱)看望父亲,一边照顾两个正在上小学的女儿,一边工作贴补家用。父亲的一个学生(浅野忠信饰)同情父亲因言获罪的遭遇,常来家中照料。母亲不仅照料一家的生活,还维持了一家平静乐观的情绪,让狱中的丈夫最大可能感受到家庭的平静和温暖,平静到可以听到两个孩子长大的声音。是母亲在最疯狂的年代营造了一个家庭价值高于一切的假象,让作为帝国大学教授的父亲在屈辱和苦难中得到最后的光亮,虽然最终父亲在狱中被折磨至死,但死前仍带着妻子不离不弃的温暖以及孩子们纯真的爱,在那个**,母亲让作为民族罪人,作为叛徒离开人世的父亲,一个本应众叛亲离的人,感受到了难能可贵的最后慰藉。
说起日本乃至亚洲的女性,尤其是母亲,几乎都是催人泪下的。不知道这是不是与亚洲妇女灾难深重有关。吉永小百合扮演的母亲,一样是那么贤良淑德勤劳坚忍,唯一的不同,或者说让人印象深刻的,就是这个日本的母亲特别重视孩子的教育,不管世界已经成什么样了都坚决要孩子们好好读书,不管是男孩子还是女孩子,这可能是其他亚洲国家的母亲做不到的。山田洋次也是透过这一点,再次表达了对日本女性的敬意,并且以谦卑的方式骄傲的暗示了一个事实:正是因为有这样的母亲,才让日本在重大的溃败下崛起,在废墟中重生。
影片还有一点就是高度的政治正确。对太平洋战争以及日本侵略亚洲这一段,山田洋次坚定的控诉了军国主义思想,立场从未改变。山田洋次还巧妙的回避了对日本人对中日关系的评论,相反倒是借着老百姓的口说了日本当时有“先打美国人然后决战德国人“这样的妄想,(当时坐在我后面看电影的德国记者哈哈笑起来,表示有趣,不在乎)但对群情激奋打中国人这样的场面就完全未表,未表的原因,倒也清楚的很,中国人创伤犹在吧。对美国投原子弹,山田洋次也没有正面抨击,却巧妙的通过设计了一个最年轻貌美、最受观众怜惜的角色,姑姑,用旁白的方式交待她回到长崎惨死的结局,而且是受了辐射一个月后饱受折磨而死,来完成了这个道德谴责。
影片的调子是苦难和温馨,情节几乎无任何新奇意外之处,该掉眼泪的地方观众都掉了,谈不上任何眼前一亮或者创新的东西,有些老套,但尽管一切都在意料之中,观众还是被打动了,尤其是被孩子们的天真,以及浅野忠信扮演的来家里帮忙的学生的性格和命运。浅野忠信演的生动。
如果从女性主义的角度挑剔一下这个片子的毛病,笔者认为,亚洲导演在歌颂亚洲女性的时候多半还是太苦大仇深了,尤其是歌颂母亲的时候,无苦不成母,越苦越高尚,很容易让人联想起贞洁牌坊——自己妻妾成群,却鼓励自己的母亲守寡,守寡时间越长越革命,事迹突出者送牌坊一座。为什么我们亚洲的母亲就不能更经常的被作为一个“人”来描写呢?为什么亚洲人表现的母亲就不能少点眼泪,多点欢乐、幽默和智慧呢?难道欢乐、幽默、智慧的母亲就那么不值得描写和歌颂吗?难道快乐的母亲就那么羞于“提倡”吗?苦难固然诗意,固然有其价值,但是过度的苦难崇拜是否会成为行为和心理暗示?我们是否有心理不健康的嫌疑?什么时候亚洲才能少歌颂一些母亲的苦难,多歌颂一些母亲作为“人”的价值?在这个问题上,笔者以为,什么时候幸福的母亲也能拿出来被歌颂了,什么时候亚洲的价值观就离理性和成熟不太远了。

影片《母亲》海报
故事主要集中在1940~1941,日本发动太平洋战争时期,日本国内全民动员发动“圣战”,全面入侵亚洲,作为故事主角的母亲的丈夫,父亲,因发表反对军国主义的言论被投进监狱,母亲本为富裕的警察局长之女,警察局长早年不满女儿嫁给穷知识分子,又嫌女婿是个“叛徒”与女儿脱离关系。此时日本国内生活日益困苦,母亲一边每天去看守所(后来是监狱)看望父亲,一边照顾两个正在上小学的女儿,一边工作贴补家用。父亲的一个学生(浅野忠信饰)同情父亲因言获罪的遭遇,常来家中照料。母亲不仅照料一家的生活,还维持了一家平静乐观的情绪,让狱中的丈夫最大可能感受到家庭的平静和温暖,平静到可以听到两个孩子长大的声音。是母亲在最疯狂的年代营造了一个家庭价值高于一切的假象,让作为帝国大学教授的父亲在屈辱和苦难中得到最后的光亮,虽然最终父亲在狱中被折磨至死,但死前仍带着妻子不离不弃的温暖以及孩子们纯真的爱,在那个**,母亲让作为民族罪人,作为叛徒离开人世的父亲,一个本应众叛亲离的人,感受到了难能可贵的最后慰藉。
说起日本乃至亚洲的女性,尤其是母亲,几乎都是催人泪下的。不知道这是不是与亚洲妇女灾难深重有关。吉永小百合扮演的母亲,一样是那么贤良淑德勤劳坚忍,唯一的不同,或者说让人印象深刻的,就是这个日本的母亲特别重视孩子的教育,不管世界已经成什么样了都坚决要孩子们好好读书,不管是男孩子还是女孩子,这可能是其他亚洲国家的母亲做不到的。山田洋次也是透过这一点,再次表达了对日本女性的敬意,并且以谦卑的方式骄傲的暗示了一个事实:正是因为有这样的母亲,才让日本在重大的溃败下崛起,在废墟中重生。
影片还有一点就是高度的政治正确。对太平洋战争以及日本侵略亚洲这一段,山田洋次坚定的控诉了军国主义思想,立场从未改变。山田洋次还巧妙的回避了对日本人对中日关系的评论,相反倒是借着老百姓的口说了日本当时有“先打美国人然后决战德国人“这样的妄想,(当时坐在我后面看电影的德国记者哈哈笑起来,表示有趣,不在乎)但对群情激奋打中国人这样的场面就完全未表,未表的原因,倒也清楚的很,中国人创伤犹在吧。对美国投原子弹,山田洋次也没有正面抨击,却巧妙的通过设计了一个最年轻貌美、最受观众怜惜的角色,姑姑,用旁白的方式交待她回到长崎惨死的结局,而且是受了辐射一个月后饱受折磨而死,来完成了这个道德谴责。
影片的调子是苦难和温馨,情节几乎无任何新奇意外之处,该掉眼泪的地方观众都掉了,谈不上任何眼前一亮或者创新的东西,有些老套,但尽管一切都在意料之中,观众还是被打动了,尤其是被孩子们的天真,以及浅野忠信扮演的来家里帮忙的学生的性格和命运。浅野忠信演的生动。
如果从女性主义的角度挑剔一下这个片子的毛病,笔者认为,亚洲导演在歌颂亚洲女性的时候多半还是太苦大仇深了,尤其是歌颂母亲的时候,无苦不成母,越苦越高尚,很容易让人联想起贞洁牌坊——自己妻妾成群,却鼓励自己的母亲守寡,守寡时间越长越革命,事迹突出者送牌坊一座。为什么我们亚洲的母亲就不能更经常的被作为一个“人”来描写呢?为什么亚洲人表现的母亲就不能少点眼泪,多点欢乐、幽默和智慧呢?难道欢乐、幽默、智慧的母亲就那么不值得描写和歌颂吗?难道快乐的母亲就那么羞于“提倡”吗?苦难固然诗意,固然有其价值,但是过度的苦难崇拜是否会成为行为和心理暗示?我们是否有心理不健康的嫌疑?什么时候亚洲才能少歌颂一些母亲的苦难,多歌颂一些母亲作为“人”的价值?在这个问题上,笔者以为,什么时候幸福的母亲也能拿出来被歌颂了,什么时候亚洲的价值观就离理性和成熟不太远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