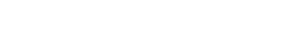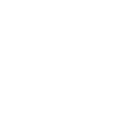来自天堂的香水——电影《香水》

影片开始,在群众的叫嚣声中我们的主人公让-巴蒂斯特•格雷诺耶拖着锒铛作响的脚镣被狼狈地提出场。执法人员宣判了对他的处罚:朝天绑在十字架上,由行刑者用铁棍活活地猛击十二下,使其臂膀关节、腿、臀部和肩膀碎裂,再钉在十字架上示众直到死去。话音刚落格拉斯的群众爆发出狂欢的期待,而观众此时更期待的是他们早就从原著中得知马上要发生一场广场群交,引起两种不同呼声的格雷诺耶此时瑟缩得像个无知少年,丝毫看不出他谋杀犯的身份。
这也是影片不断在明示或暗示着格雷诺耶应给与观众的印象:一个犯了罪的无辜者,一个邪恶的圣人。1984年,德国作家、剧作家帕德里克•徐四金完成了小说《香水》,他没有遵循流行的先锋派的写作格式,仍采用现实主义严谨的结构描绘出一个寂寂无名的天才惊世骇俗的一生,书中对气味天才格雷诺耶生死际遇的陈述也是影片的主线,但他在原作中塑造的格雷诺耶却是魔鬼与凡人混合的怪胎。也因此虽然在情节和氛围上影片《香水》努力尝试向文本《香水》靠拢,但在观看视觉化的版本时需要将两个版本通过格雷诺耶精神形象的塑造而传达的截然不同的善恶观完全区分开来:
第一个红发少女:
在1738年7月17日,也就是当年巴黎最热的一天,在法国最臭的食品交易市场上,格雷诺耶在他母亲和客人讨价还价的时候降生在她的臭鱼摊里。是巴黎最典型的臭气凝聚在他的鼻尖刺激了他求生的意识,他一声哭啼救了自己的命也把母亲送上了绞刑架。接下来在孤儿院和制皮厂的成长岁月里,格雷诺耶不自觉地努力与病毒、暴打、营养不良争夺生存的机会,也逐渐挖掘出他无以伦比的天才-他极度灵敏的嗅觉让他无须通过眼睛或语言就细致无遗地认识世界。这种天才能让他轻易地辨认并熟记上万种味道,并由此清晰地勾勒出世界具体或抽象的图样,也因此让他在马雷街加工黄李子的红发少女身上发掘到能引发精神最初狂喜的体香并把她杀死来把那气味占为己有。
马雷街的红发少女之死是格雷诺耶与文本区分开来的第一道分水岭:他在街巷里捕捉到红发少女身上的体香于是沿着气味跟踪少女,书中格雷诺耶“夜游似的”穿过走廊、后院找到了味道的根源,当他了解到这异乎寻常体味的香味的核心是纯洁的时候他心里首先想到的是“占有”这味道以便随时随地地认识它、研究它,因此他杀死少女再把她的体香嗅干的过程,格雷诺耶已经表现出一个谋杀犯应有的冷静,少女的死完全没有冲击到他的良心,体香的流失倒是他不可接受的罪恶,他的恶是由他的天才而生,是纯净的、绝对的、出自本能的恶;而影片中格雷诺耶两次循香而去他表情像是遭遇初恋的羞涩惶恐,他对少女体香的渴望更像是对圣物的膜拜,少女的死则纯粹是误杀,格雷诺耶对气味贪婪的本能此时也有了迟疑和悔意。汤姆•提克威一直打在他半边脸上的暖光和本•韦肖表现出的单纯的渴求减弱了格雷诺耶对人天生的漠视而形成的冷酷而让他的善隐约地浮现着,这个意外也为他去学习制香找到了能带动情节发展的动机。
格雷诺耶第一次杀人是为了在意识中保存香味,而他到巴尔迪尼的香水店当学徒则是因为香水店庞大的气味系统刺激他要把香味形成实质,但影片中的格雷诺耶是怀着长久地保存香味的理想来努力跻身香水世界,他尝试用各种物质来进行蒸馏以图取得像玫瑰精油那样的气味精华,目的只是证明可以把少女体香之类超然于所有自然物气味的体味变为可自由保存和使用的香水,这种理想让他的实验从文本上表现为对探索气味凝聚可能性的天生偏执转化成带着浪漫英雄气的探险。
第二个红发少女:
这种浪漫追求到格雷诺耶离开巴黎前往格拉斯学习更高级的制香工艺的路上发生了第二次的变化,这次变化对于文本的格雷诺耶或视像的格雷诺耶都是命运的转折:
格雷诺耶在途中被郊野空气清新却充满新奇的味道吸引而感到身心舒畅,这种清新让他几乎忘了出发的目的、最后躲到荒无人烟的山洞里。也就是在山洞里度过漫长的7年时间,突然意识到他能分辨出世界所有味道的鼻子居然闻不到自己的味道,因为他压根就没有味道。没有味道对于用气味认识世界的格雷诺耶来说就是无法认知或者从未存在,他第一次感到害怕,相比他自愿抛弃人世的气味来寻找孤独,因为没有体味而将永远淹没在人世的臭味中不被人注意、认同的绝对孤独更让他痛苦,正是这种缺陷、这种悖论让格雷诺耶产生既憎恨世人又渴望融入其中的矛盾感情、再到格拉斯学习制香、杀人来制造能统御人类的奇香也有了顺理成章的动机,但影片简省了大段文本中关于山洞生活到寻求体味(自我)的内容,红发少女闻不到他的体味而对他视而不见的噩梦直接把格雷诺耶的理想变成被世人认识的欲望。这段删减虽然也合情理,但是他身上的悲剧性和疯狂也因此大打折扣。
代替马雷街少女成为其新缪斯的红发少女罗拉突如其来的体香也被称作“似乎是上帝对他的恩赐”,格雷诺耶往后的谋杀也越来越浪漫、越来越让人期待,他犯下的罪反而一再反衬出他的纯真和他作为最伟大的香水专家的重要性。影片并没有像文本那样让格雷诺耶轻易地把取香的欲望变作杀人不眨眼的绝对邪恶,他第一次用油脂取香的时候对待妓女的态度礼貌谦卑,杀人的手段虽残忍但影片却把重点放在细致地表现他如何用朝圣的神态取香,谋杀引起的恐惧很快被散发着芳香的工艺掩盖,他的作恶又是一次意外,是为实现更神圣理想的不得已(这次迟疑和前一次杀害花农少女的直截了当却又自相矛盾)。
罗拉是格拉斯最美的女孩,也是格雷诺耶最苦苦追求的猎物。她既是格雷诺耶锁定处女体香创造的香水的芬芳核心,也是影片把格雷诺耶的谋杀神圣化的道具之一,不仅是在他追寻她体香时流露出的近似于爱情的激动(甚至于悲伤)的表情、他结束她生命前不知是为什么动摇的一丝犹豫,罗拉的父亲打开房门时罗拉尸体散发出的耀眼金光更是把这一次次谋杀总结成一场用人间至纯至美之物献祭的祭祀。
第三个红发少女:
作为“祭司”的格雷诺耶直到上刑场也从未显得猥琐可憎。刑场上为即将开始的暴行而兴奋躁动的人群在他(他已悄悄抹上成功混合13个少女体香的香水)来到后突然鸦雀无声,一瞬间他在人们的眼里成了纯洁的天使,势在必行的行刑成了集体膜拜,这时的本•韦肖真正展现出他本来的-也是故事里被香水味迷惑的人们眼里-王子般的高贵俊俏,刚还在吵闹作一团的愚蠢群众都向行刑台上的他伸出虔诚的手臂,紧接着像发现了被强大的爱感召似的所有的人都互相拥抱、亲昵。虽然文本和视像中的格雷诺耶都明白奇香的魅力已经超越了所有人间知识、宗教的法力,但被一堆黄李子再次激起的对马雷街红发少女的回忆和想象与本•韦肖的格雷诺耶流下了眼泪则彻底把他和文本中目睹淫乱的人群在内心发出恶心的嘲笑的格雷诺耶分开了。马雷街的少女曾反复出现在决定格雷诺耶制香生涯的几个关键点,这最后的一次幻想格雷诺耶从对她嗅觉上的依恋转化到凡俗的肌肤之亲,他是被眼前的爱欲的海洋触动还是内心的世俗欲望被唤醒不得而知,但与文本里此刻回想着自己饱受折磨的童年,只能靠憎恨的力量才得以生存的格雷诺耶相比,他心中泛起的是被爱和爱的需要,他的善良又一次通过犹如他初恋的红发少女战胜了他的本能,他也再次感到绝对的孤独,这和文本中同样被强调的孤独完全不同:那是因为他清醒地意识到迷惑众生的胜利是虚幻的,他永远不可能被视作一个人;而眼前的格雷诺耶则苦于罪恶感和无法作为一个人来赎罪。
因此同样带着对理想的绝望、同样是回到和出生时一样恶臭的贫民区、同样把香水浇到身上让疯狂被吸引的人们用莫名的热爱吃掉自己,文本的格雷诺耶因为寻找、建立自我的失败,影片的格雷诺耶是因为对爱的渴望和绝望,他的结局也因此显得悲壮。
影片的音乐也从头到尾为塑造格雷诺耶悲壮形象推波助澜,虽然影片“一个谋杀犯的故事”的副题让人感到阴森,影片中无处不在的宏伟庄严的交响乐赋予“谋杀”二字隆重的仪式感,而每次谋杀及用尸体制香的过程都伴随着犹如天籁的咏叹;群交场面咏叹再次久久回荡,这个在书中被形容为“地狱”、本应比《暴帝卡尼古拉》里“群臣共欢”过犹不及的场面却让人有种“天下大同”的幸福错觉。这些既是格雷诺耶当时内心的感受也是影片促使观众对这个谋杀犯表示欣赏和同情的手段之一。
一瓶不过不失的“香水”
《香水》在宣布开拍之前就马上激起了激烈的讨论,此类名著改编作品多会让人们把眼光放在是否能忠实原著精神、是否能重现文字精彩;从出版商手中几经艰辛取得版权后,“德国电影教父”伯尔尼•伊钦格请到《玫瑰之名》的编剧安德鲁·柏金改编剧本,据称前后改动了20多次最终找到创作的核心,也是谋杀的动机—“想被认知的迫切感和欲望”,但《香水》在精神上省略了原作用对绝对的恶精细的描写表达的讽刺,试图温和地半是神化半是人性化格雷诺耶,却失去了邪恶和宿命具备的趣味。在争夺影片改编权的时候,对人之美、恶、永恒很有一套哲学理念的斯坦利•库布里克也曾在徐四金意向范围内,可惜最终未能如愿,如果这部作品交由他拍摄,原作中的的邪行可能又会呈现另一种惊人的模样。
但撇开原作来看,《香水》算是一部合格的异色惊悚片,实际上更多读过原著的人关注的是原作用文字就完成了嗅觉上的完美体验,电影版如何用视觉效果传递嗅觉效果;在处理这一点时,伊钦格钦点执导的汤姆•提克威(《疾走罗拉》)又一次发挥了他镜头的想象力,他在这个古装片里运用不少现代的镜头转换方式,镜头以呼吸的节奏在鼻子嗅入动作的特写和各种物质、场景间切换传达了质感在嗅觉上的体现;用特写、慢镜头巨细无遗地展示蒸馏、提取香料,包括用油脂在人体取香等专业的制香过程,香味仿佛慢慢渗透在画面;而各种典型的象征物-如一大片薰衣草花田、放满上百种香料的仓库、烂肉、内脏和呕吐物等等-都能迅速激起嗅觉的反应。本•韦肖的表演使格雷诺耶的形象鲜活起来,他把这个角色的天真、单纯、执著、冷漠贯彻至终,尤其在缺少台词辅助时,光凭眼神和肢体-尤其是鼻子-动作就演绎出对虚无的气味的敏感和狂热。

影片开始,在群众的叫嚣声中我们的主人公让-巴蒂斯特•格雷诺耶拖着锒铛作响的脚镣被狼狈地提出场。执法人员宣判了对他的处罚:朝天绑在十字架上,由行刑者用铁棍活活地猛击十二下,使其臂膀关节、腿、臀部和肩膀碎裂,再钉在十字架上示众直到死去。话音刚落格拉斯的群众爆发出狂欢的期待,而观众此时更期待的是他们早就从原著中得知马上要发生一场广场群交,引起两种不同呼声的格雷诺耶此时瑟缩得像个无知少年,丝毫看不出他谋杀犯的身份。
这也是影片不断在明示或暗示着格雷诺耶应给与观众的印象:一个犯了罪的无辜者,一个邪恶的圣人。1984年,德国作家、剧作家帕德里克•徐四金完成了小说《香水》,他没有遵循流行的先锋派的写作格式,仍采用现实主义严谨的结构描绘出一个寂寂无名的天才惊世骇俗的一生,书中对气味天才格雷诺耶生死际遇的陈述也是影片的主线,但他在原作中塑造的格雷诺耶却是魔鬼与凡人混合的怪胎。也因此虽然在情节和氛围上影片《香水》努力尝试向文本《香水》靠拢,但在观看视觉化的版本时需要将两个版本通过格雷诺耶精神形象的塑造而传达的截然不同的善恶观完全区分开来:
第一个红发少女:
在1738年7月17日,也就是当年巴黎最热的一天,在法国最臭的食品交易市场上,格雷诺耶在他母亲和客人讨价还价的时候降生在她的臭鱼摊里。是巴黎最典型的臭气凝聚在他的鼻尖刺激了他求生的意识,他一声哭啼救了自己的命也把母亲送上了绞刑架。接下来在孤儿院和制皮厂的成长岁月里,格雷诺耶不自觉地努力与病毒、暴打、营养不良争夺生存的机会,也逐渐挖掘出他无以伦比的天才-他极度灵敏的嗅觉让他无须通过眼睛或语言就细致无遗地认识世界。这种天才能让他轻易地辨认并熟记上万种味道,并由此清晰地勾勒出世界具体或抽象的图样,也因此让他在马雷街加工黄李子的红发少女身上发掘到能引发精神最初狂喜的体香并把她杀死来把那气味占为己有。
马雷街的红发少女之死是格雷诺耶与文本区分开来的第一道分水岭:他在街巷里捕捉到红发少女身上的体香于是沿着气味跟踪少女,书中格雷诺耶“夜游似的”穿过走廊、后院找到了味道的根源,当他了解到这异乎寻常体味的香味的核心是纯洁的时候他心里首先想到的是“占有”这味道以便随时随地地认识它、研究它,因此他杀死少女再把她的体香嗅干的过程,格雷诺耶已经表现出一个谋杀犯应有的冷静,少女的死完全没有冲击到他的良心,体香的流失倒是他不可接受的罪恶,他的恶是由他的天才而生,是纯净的、绝对的、出自本能的恶;而影片中格雷诺耶两次循香而去他表情像是遭遇初恋的羞涩惶恐,他对少女体香的渴望更像是对圣物的膜拜,少女的死则纯粹是误杀,格雷诺耶对气味贪婪的本能此时也有了迟疑和悔意。汤姆•提克威一直打在他半边脸上的暖光和本•韦肖表现出的单纯的渴求减弱了格雷诺耶对人天生的漠视而形成的冷酷而让他的善隐约地浮现着,这个意外也为他去学习制香找到了能带动情节发展的动机。
格雷诺耶第一次杀人是为了在意识中保存香味,而他到巴尔迪尼的香水店当学徒则是因为香水店庞大的气味系统刺激他要把香味形成实质,但影片中的格雷诺耶是怀着长久地保存香味的理想来努力跻身香水世界,他尝试用各种物质来进行蒸馏以图取得像玫瑰精油那样的气味精华,目的只是证明可以把少女体香之类超然于所有自然物气味的体味变为可自由保存和使用的香水,这种理想让他的实验从文本上表现为对探索气味凝聚可能性的天生偏执转化成带着浪漫英雄气的探险。
第二个红发少女:
这种浪漫追求到格雷诺耶离开巴黎前往格拉斯学习更高级的制香工艺的路上发生了第二次的变化,这次变化对于文本的格雷诺耶或视像的格雷诺耶都是命运的转折:
格雷诺耶在途中被郊野空气清新却充满新奇的味道吸引而感到身心舒畅,这种清新让他几乎忘了出发的目的、最后躲到荒无人烟的山洞里。也就是在山洞里度过漫长的7年时间,突然意识到他能分辨出世界所有味道的鼻子居然闻不到自己的味道,因为他压根就没有味道。没有味道对于用气味认识世界的格雷诺耶来说就是无法认知或者从未存在,他第一次感到害怕,相比他自愿抛弃人世的气味来寻找孤独,因为没有体味而将永远淹没在人世的臭味中不被人注意、认同的绝对孤独更让他痛苦,正是这种缺陷、这种悖论让格雷诺耶产生既憎恨世人又渴望融入其中的矛盾感情、再到格拉斯学习制香、杀人来制造能统御人类的奇香也有了顺理成章的动机,但影片简省了大段文本中关于山洞生活到寻求体味(自我)的内容,红发少女闻不到他的体味而对他视而不见的噩梦直接把格雷诺耶的理想变成被世人认识的欲望。这段删减虽然也合情理,但是他身上的悲剧性和疯狂也因此大打折扣。
代替马雷街少女成为其新缪斯的红发少女罗拉突如其来的体香也被称作“似乎是上帝对他的恩赐”,格雷诺耶往后的谋杀也越来越浪漫、越来越让人期待,他犯下的罪反而一再反衬出他的纯真和他作为最伟大的香水专家的重要性。影片并没有像文本那样让格雷诺耶轻易地把取香的欲望变作杀人不眨眼的绝对邪恶,他第一次用油脂取香的时候对待妓女的态度礼貌谦卑,杀人的手段虽残忍但影片却把重点放在细致地表现他如何用朝圣的神态取香,谋杀引起的恐惧很快被散发着芳香的工艺掩盖,他的作恶又是一次意外,是为实现更神圣理想的不得已(这次迟疑和前一次杀害花农少女的直截了当却又自相矛盾)。
罗拉是格拉斯最美的女孩,也是格雷诺耶最苦苦追求的猎物。她既是格雷诺耶锁定处女体香创造的香水的芬芳核心,也是影片把格雷诺耶的谋杀神圣化的道具之一,不仅是在他追寻她体香时流露出的近似于爱情的激动(甚至于悲伤)的表情、他结束她生命前不知是为什么动摇的一丝犹豫,罗拉的父亲打开房门时罗拉尸体散发出的耀眼金光更是把这一次次谋杀总结成一场用人间至纯至美之物献祭的祭祀。
第三个红发少女:
作为“祭司”的格雷诺耶直到上刑场也从未显得猥琐可憎。刑场上为即将开始的暴行而兴奋躁动的人群在他(他已悄悄抹上成功混合13个少女体香的香水)来到后突然鸦雀无声,一瞬间他在人们的眼里成了纯洁的天使,势在必行的行刑成了集体膜拜,这时的本•韦肖真正展现出他本来的-也是故事里被香水味迷惑的人们眼里-王子般的高贵俊俏,刚还在吵闹作一团的愚蠢群众都向行刑台上的他伸出虔诚的手臂,紧接着像发现了被强大的爱感召似的所有的人都互相拥抱、亲昵。虽然文本和视像中的格雷诺耶都明白奇香的魅力已经超越了所有人间知识、宗教的法力,但被一堆黄李子再次激起的对马雷街红发少女的回忆和想象与本•韦肖的格雷诺耶流下了眼泪则彻底把他和文本中目睹淫乱的人群在内心发出恶心的嘲笑的格雷诺耶分开了。马雷街的少女曾反复出现在决定格雷诺耶制香生涯的几个关键点,这最后的一次幻想格雷诺耶从对她嗅觉上的依恋转化到凡俗的肌肤之亲,他是被眼前的爱欲的海洋触动还是内心的世俗欲望被唤醒不得而知,但与文本里此刻回想着自己饱受折磨的童年,只能靠憎恨的力量才得以生存的格雷诺耶相比,他心中泛起的是被爱和爱的需要,他的善良又一次通过犹如他初恋的红发少女战胜了他的本能,他也再次感到绝对的孤独,这和文本中同样被强调的孤独完全不同:那是因为他清醒地意识到迷惑众生的胜利是虚幻的,他永远不可能被视作一个人;而眼前的格雷诺耶则苦于罪恶感和无法作为一个人来赎罪。
因此同样带着对理想的绝望、同样是回到和出生时一样恶臭的贫民区、同样把香水浇到身上让疯狂被吸引的人们用莫名的热爱吃掉自己,文本的格雷诺耶因为寻找、建立自我的失败,影片的格雷诺耶是因为对爱的渴望和绝望,他的结局也因此显得悲壮。
影片的音乐也从头到尾为塑造格雷诺耶悲壮形象推波助澜,虽然影片“一个谋杀犯的故事”的副题让人感到阴森,影片中无处不在的宏伟庄严的交响乐赋予“谋杀”二字隆重的仪式感,而每次谋杀及用尸体制香的过程都伴随着犹如天籁的咏叹;群交场面咏叹再次久久回荡,这个在书中被形容为“地狱”、本应比《暴帝卡尼古拉》里“群臣共欢”过犹不及的场面却让人有种“天下大同”的幸福错觉。这些既是格雷诺耶当时内心的感受也是影片促使观众对这个谋杀犯表示欣赏和同情的手段之一。
一瓶不过不失的“香水”
《香水》在宣布开拍之前就马上激起了激烈的讨论,此类名著改编作品多会让人们把眼光放在是否能忠实原著精神、是否能重现文字精彩;从出版商手中几经艰辛取得版权后,“德国电影教父”伯尔尼•伊钦格请到《玫瑰之名》的编剧安德鲁·柏金改编剧本,据称前后改动了20多次最终找到创作的核心,也是谋杀的动机—“想被认知的迫切感和欲望”,但《香水》在精神上省略了原作用对绝对的恶精细的描写表达的讽刺,试图温和地半是神化半是人性化格雷诺耶,却失去了邪恶和宿命具备的趣味。在争夺影片改编权的时候,对人之美、恶、永恒很有一套哲学理念的斯坦利•库布里克也曾在徐四金意向范围内,可惜最终未能如愿,如果这部作品交由他拍摄,原作中的的邪行可能又会呈现另一种惊人的模样。
但撇开原作来看,《香水》算是一部合格的异色惊悚片,实际上更多读过原著的人关注的是原作用文字就完成了嗅觉上的完美体验,电影版如何用视觉效果传递嗅觉效果;在处理这一点时,伊钦格钦点执导的汤姆•提克威(《疾走罗拉》)又一次发挥了他镜头的想象力,他在这个古装片里运用不少现代的镜头转换方式,镜头以呼吸的节奏在鼻子嗅入动作的特写和各种物质、场景间切换传达了质感在嗅觉上的体现;用特写、慢镜头巨细无遗地展示蒸馏、提取香料,包括用油脂在人体取香等专业的制香过程,香味仿佛慢慢渗透在画面;而各种典型的象征物-如一大片薰衣草花田、放满上百种香料的仓库、烂肉、内脏和呕吐物等等-都能迅速激起嗅觉的反应。本•韦肖的表演使格雷诺耶的形象鲜活起来,他把这个角色的天真、单纯、执著、冷漠贯彻至终,尤其在缺少台词辅助时,光凭眼神和肢体-尤其是鼻子-动作就演绎出对虚无的气味的敏感和狂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