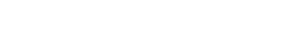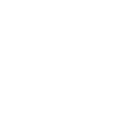X
xiaojingdong
游客
初到狮城的那个夜晚,在宽敞明亮的樟宜机场接客大厅里,多语言多肤色多民族和睦的场景令我感到新奇,忘记了飞机晚点达七个多小时的烦闷与旅途疲劳,真想把这一切都尽收眼底.
先生早已等侯在机场,熟悉的身影,熟悉的乡音,熟悉的动作,一切都安排就绪。在机场观光一番,我们来到机场出口大厅。
大厅门口的出租车已经排成了一条长龙,出租汽车也鱼贯而入,人们秩序井然,很快便轮到了我们。司机下车热情地用英语和我们打招呼,迅速地把行李搬上后车箱。随着车子在高速公路上飞驰着,沿途两侧热带植物在明亮的路灯辉映下并排耸立,迅速地向后倒退去.
司机是个中等身材的中年男士,快人快语,十分健谈。他先热情地用英语问我们是日本人还是韩国人。当我们告诉他我们是中国人时,他立刻改换用华语问我们是否从美国过来的。我们告诉他我们来自中国的北方城市。他立刻抢过话头说:“哦!知道,知道,北京是中国的首都……”
汽车拐了几个弯,停在了勿洛南组屋区的一条小马路边上,电子屏幕上显示:$9.6。先生把一张十元的钞票交给他,他伸手示意不必找钱了,说了一声:“谢谢!祝你们好运!”便驾着车子,向前驶去。
夜晚的组屋区,到处灯火通明。先生提着全部的行李,我跟在其后,来到了一座组屋电梯的门口。他转回头,对我说:“一会儿,你要有思想准备,这可是你选租的人家呀!”我在想:他要我有什么思想准备呢?电梯上了六楼,穿过长长的走廊,来到了一个角头的房门口。先生拿出钥匙,先打开外面的铁门,再打开里面的木门。
客厅里的灯光有些暗淡,一股说不出的味道钻入了鼻孔,令我不禁向后倒退了半步。迎接我们的是三个孩子,他们的皮肤乌黑发亮,一双大大的眼睛,忽闪忽闪的,睫毛又长又卷,乌黑卷卷的头发,随着他们的跳跃也在头上跳跃着。能感觉到他们的热情兴奋与欣喜,然而他们讲的英语,我却一句也听不懂。一位个子不高的印度中年妇女,热情地从房间里走出来,和我们打着招呼。
先生嘱咐我把鞋脱了,光着脚进屋,说是这里的习俗。我环顾着周围,这是一个三房式组屋,地板是带花纹的大理石做的,光着脚踩在上面,凉丝丝的.客厅是个长方形,大约十六平方米左右,靠墙放着一套黑色皮沙发,斜对面靠窗的下方摆放着一个茶几,上面有一台24吋的彩色电视机,电视里正在播放着印度影片。走进我们租住的大房间,除了一张沙发床及厚厚的床垫,还有一个白色的小床头柜,地上放着一架台式电风扇。
行李刚放在了地上,门便被敲开了,只见印族女房东和三个孩子,把一个大衣柜推在了门口,要让我们用。我走出来,探头看了一下隔壁主人的小房间,里面除了两个垫子外,空空如也。衣物堆了一地,显得杂乱无章。我立刻明白了:他们把自己唯一的大衣柜腾出来给我们用,自己什么都没有。一股暖流通过全身,除了深深的感动,还有一种复杂难言的感受:原来在所谓先进国家,居然还有这么贫困的人民。
在厨房里转了一圈,除了基本的灶具,墙壁的一周镶嵌着吊柜,女房东主动打开其中一扇吊柜的门,对我们说:这是专门为我们腾空使用的。冰箱不大,她为我们腾出了一个空格,告诉我们可以储存些食物,但最好不要有肉食。
厨房的侧面,有一个厕所和一个冲凉房,里面都不大,估计最多有两平方米,门呈灰色,用铝合金做的。引起我警惕的是两扇门高并未到屋顶,空间大概有一尺多。还好,先生告诉我:这家的男主人是印度籍,平时不在新加坡,女房东在一家电子公司工作,她的母亲就住在隔壁的组屋,孩子经常放在她母亲家,因此家中常常上演“空城计”。
来狮城前,我一再嘱咐先生,要租一家不会讲华语的家庭,以便使我能尽快过英语关,融入当地的环境。听说是印度人,总以为是那种电影中见到的白种印度人,却没想到跟自己的想象大相径庭;想练习英语口语,更没想到他们讲的英语与在国内学的英语发音差得十万八千里,现在自己跟聋子没有什么分别;想象着房东的家里不一定要豪华,毕竟我们只是晚上住一住,出人意料的是把基本的家具借给我们暂用,他们已是家徒四壁。
冲凉后,吃过随身带来的简单食物,躺在软软的,令人极不习惯的床上,外面明亮的灯光照进了没有窗帘的屋内,如同白昼,想着留在国内的年幼女儿,心里有说不出的感受,脑子十分清醒,难以入眠……
先生早已等侯在机场,熟悉的身影,熟悉的乡音,熟悉的动作,一切都安排就绪。在机场观光一番,我们来到机场出口大厅。
大厅门口的出租车已经排成了一条长龙,出租汽车也鱼贯而入,人们秩序井然,很快便轮到了我们。司机下车热情地用英语和我们打招呼,迅速地把行李搬上后车箱。随着车子在高速公路上飞驰着,沿途两侧热带植物在明亮的路灯辉映下并排耸立,迅速地向后倒退去.
司机是个中等身材的中年男士,快人快语,十分健谈。他先热情地用英语问我们是日本人还是韩国人。当我们告诉他我们是中国人时,他立刻改换用华语问我们是否从美国过来的。我们告诉他我们来自中国的北方城市。他立刻抢过话头说:“哦!知道,知道,北京是中国的首都……”
汽车拐了几个弯,停在了勿洛南组屋区的一条小马路边上,电子屏幕上显示:$9.6。先生把一张十元的钞票交给他,他伸手示意不必找钱了,说了一声:“谢谢!祝你们好运!”便驾着车子,向前驶去。
夜晚的组屋区,到处灯火通明。先生提着全部的行李,我跟在其后,来到了一座组屋电梯的门口。他转回头,对我说:“一会儿,你要有思想准备,这可是你选租的人家呀!”我在想:他要我有什么思想准备呢?电梯上了六楼,穿过长长的走廊,来到了一个角头的房门口。先生拿出钥匙,先打开外面的铁门,再打开里面的木门。
客厅里的灯光有些暗淡,一股说不出的味道钻入了鼻孔,令我不禁向后倒退了半步。迎接我们的是三个孩子,他们的皮肤乌黑发亮,一双大大的眼睛,忽闪忽闪的,睫毛又长又卷,乌黑卷卷的头发,随着他们的跳跃也在头上跳跃着。能感觉到他们的热情兴奋与欣喜,然而他们讲的英语,我却一句也听不懂。一位个子不高的印度中年妇女,热情地从房间里走出来,和我们打着招呼。
先生嘱咐我把鞋脱了,光着脚进屋,说是这里的习俗。我环顾着周围,这是一个三房式组屋,地板是带花纹的大理石做的,光着脚踩在上面,凉丝丝的.客厅是个长方形,大约十六平方米左右,靠墙放着一套黑色皮沙发,斜对面靠窗的下方摆放着一个茶几,上面有一台24吋的彩色电视机,电视里正在播放着印度影片。走进我们租住的大房间,除了一张沙发床及厚厚的床垫,还有一个白色的小床头柜,地上放着一架台式电风扇。
行李刚放在了地上,门便被敲开了,只见印族女房东和三个孩子,把一个大衣柜推在了门口,要让我们用。我走出来,探头看了一下隔壁主人的小房间,里面除了两个垫子外,空空如也。衣物堆了一地,显得杂乱无章。我立刻明白了:他们把自己唯一的大衣柜腾出来给我们用,自己什么都没有。一股暖流通过全身,除了深深的感动,还有一种复杂难言的感受:原来在所谓先进国家,居然还有这么贫困的人民。
在厨房里转了一圈,除了基本的灶具,墙壁的一周镶嵌着吊柜,女房东主动打开其中一扇吊柜的门,对我们说:这是专门为我们腾空使用的。冰箱不大,她为我们腾出了一个空格,告诉我们可以储存些食物,但最好不要有肉食。
厨房的侧面,有一个厕所和一个冲凉房,里面都不大,估计最多有两平方米,门呈灰色,用铝合金做的。引起我警惕的是两扇门高并未到屋顶,空间大概有一尺多。还好,先生告诉我:这家的男主人是印度籍,平时不在新加坡,女房东在一家电子公司工作,她的母亲就住在隔壁的组屋,孩子经常放在她母亲家,因此家中常常上演“空城计”。
来狮城前,我一再嘱咐先生,要租一家不会讲华语的家庭,以便使我能尽快过英语关,融入当地的环境。听说是印度人,总以为是那种电影中见到的白种印度人,却没想到跟自己的想象大相径庭;想练习英语口语,更没想到他们讲的英语与在国内学的英语发音差得十万八千里,现在自己跟聋子没有什么分别;想象着房东的家里不一定要豪华,毕竟我们只是晚上住一住,出人意料的是把基本的家具借给我们暂用,他们已是家徒四壁。
冲凉后,吃过随身带来的简单食物,躺在软软的,令人极不习惯的床上,外面明亮的灯光照进了没有窗帘的屋内,如同白昼,想着留在国内的年幼女儿,心里有说不出的感受,脑子十分清醒,难以入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