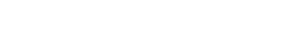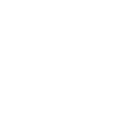我不知道她的名字,也不知道她住在哪里,只知道她长得很丑,经常穿梭在校园里靠捡垃圾为生。
这个人被我唤做“卡西莫多”。
只因为她长得像《巴黎圣母院》里面的那个丑陋的敲钟人。四十几岁,虽不跛脚,但她走路的样子却很畸形,有点歪歪斜斜的样子。背有点驼。但更为触目惊心的是她那布满皱纹的脸上赫然垂下一个大大的肉球。
对于她我并不带有一丝鄙意,应该是好奇吧。我关注她,就像在关注生活的另一面。
走在校园里经常会碰见她的身影。她,永远披着那件土布卡其红外套,穿着不合脚的大大脏脏的运动鞋,右肩背着一个蛇皮袋,里面充满了矿泉水瓶还有些废纸。她走得很快,可是每到一个垃圾箱,她总会停下匆匆的脚步,往里面使劲地掏东西。矿泉水瓶往往会给她带来很大的惊喜。我见过她从垃圾桶里掏出甘蔗来啃,但是从不见她吃里面的剩饭剩菜。她不是乞丐,只是一个拾荒者。
她应该还有一个家。
那天傍晚晚霞很红的时候,在学院路的余晖中,我看到她和一个跟她一样长得很丑的男人在努力地推着一辆垃圾车。她像个有力的纤夫在前面拉,那个男人在后面使劲地推。一路上,他们没有什么言语和表情,就像是木偶人,生活牵着他们走着。同伴不禁感叹着他们生活的艰辛。可我在想,也许这对于他们来说,这是生活给他们的安排,经常要做的事情,很正常不过吧,安于现状了也就不会觉得痛苦了。但是稍微的改变也许就会让他们觉得很恐慌,就像现在,要是车子突然翻了,他们真不知道应该怎么办吧。
一次看到她手里小心翼翼地捧着两个盒饭,朝圣般的,满是皱纹的脸上散发着异常的光彩,像一只老母鸡觅到食物般兴奋地朝外面疾走。我想她兴许是很久没吃到盒饭了吧,就是简单的盒饭在她的眼里就变成了奢侈品,她舍不得吃,要拿回去给她的丈夫或是儿女们吃吧。她有儿女吗?也许有吧,因为我明明看到的是一个母亲闪烁着的飞扬的神采。
总是看到她的背影,永远是那件土红色的外套,肩上一小袋的废品,还是走得有点畸形,有点凄凉。我看见她穿过小路,往她的“家”的方向走去,留下一个永远都弄不懂的问号。
只有一次她朝我正面走过来。那时的我正在犹豫着我的事情,不小心抬头,发现了那双黑黝黝的但显麻木的眼睛。我立刻低下头,再也不敢看她,那个触目惊心的肉球也似乎老在眼前晃动。
每次看见她,我总会猜想她的一切。她到底是谁呢,从何来到何去,她是不是能过着正常的生活,有丈夫疼爱儿女孝顺呢?她的背后有什么辛酸的故事呢?她这样活着会不会感到很痛苦呢?几天不见,她是不是生病了呢?我猜想着,也许这是她正常的生活,就是生活练就的,生活让她成了一具木偶,让她每天都穿梭在校园里,做永远的拾荒者。我不知道她的精神世界,也不能去侵犯她的世界。又或许我的猜想是错的,或许,她在感谢上帝给予她的一切,包括每天捡得的垃圾,难得一见的盒饭……
我该对她充满着很深的敬畏,就像是对生命的敬畏。
凝神思绪中,她像清风般从我的身边飘过,留给我一个永恒的背影
这个人被我唤做“卡西莫多”。
只因为她长得像《巴黎圣母院》里面的那个丑陋的敲钟人。四十几岁,虽不跛脚,但她走路的样子却很畸形,有点歪歪斜斜的样子。背有点驼。但更为触目惊心的是她那布满皱纹的脸上赫然垂下一个大大的肉球。
对于她我并不带有一丝鄙意,应该是好奇吧。我关注她,就像在关注生活的另一面。
走在校园里经常会碰见她的身影。她,永远披着那件土布卡其红外套,穿着不合脚的大大脏脏的运动鞋,右肩背着一个蛇皮袋,里面充满了矿泉水瓶还有些废纸。她走得很快,可是每到一个垃圾箱,她总会停下匆匆的脚步,往里面使劲地掏东西。矿泉水瓶往往会给她带来很大的惊喜。我见过她从垃圾桶里掏出甘蔗来啃,但是从不见她吃里面的剩饭剩菜。她不是乞丐,只是一个拾荒者。
她应该还有一个家。
那天傍晚晚霞很红的时候,在学院路的余晖中,我看到她和一个跟她一样长得很丑的男人在努力地推着一辆垃圾车。她像个有力的纤夫在前面拉,那个男人在后面使劲地推。一路上,他们没有什么言语和表情,就像是木偶人,生活牵着他们走着。同伴不禁感叹着他们生活的艰辛。可我在想,也许这对于他们来说,这是生活给他们的安排,经常要做的事情,很正常不过吧,安于现状了也就不会觉得痛苦了。但是稍微的改变也许就会让他们觉得很恐慌,就像现在,要是车子突然翻了,他们真不知道应该怎么办吧。
一次看到她手里小心翼翼地捧着两个盒饭,朝圣般的,满是皱纹的脸上散发着异常的光彩,像一只老母鸡觅到食物般兴奋地朝外面疾走。我想她兴许是很久没吃到盒饭了吧,就是简单的盒饭在她的眼里就变成了奢侈品,她舍不得吃,要拿回去给她的丈夫或是儿女们吃吧。她有儿女吗?也许有吧,因为我明明看到的是一个母亲闪烁着的飞扬的神采。
总是看到她的背影,永远是那件土红色的外套,肩上一小袋的废品,还是走得有点畸形,有点凄凉。我看见她穿过小路,往她的“家”的方向走去,留下一个永远都弄不懂的问号。
只有一次她朝我正面走过来。那时的我正在犹豫着我的事情,不小心抬头,发现了那双黑黝黝的但显麻木的眼睛。我立刻低下头,再也不敢看她,那个触目惊心的肉球也似乎老在眼前晃动。
每次看见她,我总会猜想她的一切。她到底是谁呢,从何来到何去,她是不是能过着正常的生活,有丈夫疼爱儿女孝顺呢?她的背后有什么辛酸的故事呢?她这样活着会不会感到很痛苦呢?几天不见,她是不是生病了呢?我猜想着,也许这是她正常的生活,就是生活练就的,生活让她成了一具木偶,让她每天都穿梭在校园里,做永远的拾荒者。我不知道她的精神世界,也不能去侵犯她的世界。又或许我的猜想是错的,或许,她在感谢上帝给予她的一切,包括每天捡得的垃圾,难得一见的盒饭……
我该对她充满着很深的敬畏,就像是对生命的敬畏。
凝神思绪中,她像清风般从我的身边飘过,留给我一个永恒的背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