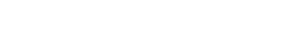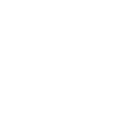元宵节,是一个热闹欢乐的节日。人们张灯结彩,出门赏月,燃放烟花,舞龙舞狮,赏灯猜谜,扭秧歌,吃元宵,古代的诗人们有许多的精彩的描述,唐代的苏味道的《正月十五夜》如此说“火树银花合,星桥铁锁开,灯树千光照,明月逐人来”,元代元好问的《京都元夕》如是说“袨服华妆着处逢 ,六街灯火闹儿童 。长衫我亦何为者 ,也在游人笑语中 ”。
元宵节,又是一个浪漫柔情的节日,对妇女和青年人尤其是这样。封建社会里,妇女是没有独立外出的权利的,但是,元宵节是可以出来游玩的。她们结伴而行或走墙边,或过桥,走郊外,目的是驱病除灾,也起到了放松身心、愉悦情志的作用。街市赏灯,也为青年男女提供了与情人相会的机会,他们会在火树银花前眉目传情,在朦胧月光下倾吐心曲,在佛寺道观里为爱许愿。怪不得有人称元宵节为中国的“情人节”。对于这一点,宋词有名篇佳句展现。
“词别是一家”,婉约派主导的宋代词坛,抒情为其“当行本色”,词人更擅长刻画深婉蕴籍、幽深细腻的情感世界,意境较诗更精美清幽,情感更坦率真挚,画面更秾丽光艳。许多词人写下过情意绸缪的“元夕”词。
欧阳修的《生查子·元夕》意味隽永:
去年元夜时,花市灯如昼。月上柳梢头,人约黄昏后。
今年元夜时,月与灯依旧。不见去年人,泪湿春衫袖!
李白以降,历花间、南唐词派,直至两宋,男性词人多采用代言体,表现闺愁怨情,其抒情之哀婉缠绵,以至有甚于女词人。欧阳修的《元夕》,模拟失意女子的口吻,以细腻的笔触探入其幽深微妙的心灵底处,挖掘出积郁已久的幽愁暗恨,言简意赅,耐人寻味。
这首词通篇运用白描,章法上有似民歌的重章叠唱,上下两片成今昔对比,所以,其境皆素淡清新,其意却甘苦迥异。
站在现实的立足点上,回思去年今日,是中国诗人怀旧的一种传统的做法。他们的记忆永远是选择性的:崔护就将对城南旧事的无限思绪,定格于“人面桃花相映红”的画面上,令人想见往日那深挚热烈的一幕幕;欧阳修则先取“花市灯如昼”作为背景,那火树银花,熙来攘往的元宵节图景,是俗世狂欢的场面,是旧日中国难得的良辰美景。按尼采的话来说,它是日神阿波罗与酒神迪奥尼索斯的会合,有幻境,也有醉境,有对习惯乃至礼教的超越,更为有情人创设了相会的最佳时机——别人欢乐,他们可以闹中取静,见机行事,以遂平日之愿——面孔看似古板冰冷的都市,也有其温情脉脉开通的一面。
读者期待有那惊世骇俗的相见场面出现,然而,欧阳修却把它化为一片“空白”,留给我们悬念,留给我们想象的空间,这叫做“避实就虚”吧?他只写了此前的两个时辰:“月上柳梢头”,那是日入的酉时,“他”和“她”,在都城的一东一西,共同仰望着东升的月亮,它缓缓爬上来,挂在了梢尖初嫩的杨柳之上。此刻,春风骀荡,春机乍现,他们心旌摇荡,两情相悦,心有灵犀,只言片语,即已暗寄款款深情,只待婵娟高挂,早遂夙愿。两个人坐立不安,搔首踟蹰,因为此前禁锢得越久,束缚得越苦,此时就更期盼自由之欢,相聚之乐;可是,必待黄昏戌时后,方可腾出空间和时间给两位有情人,那时,他们才可借众人的忘我的狂欢,掩蔽悦情的情偶相聚。但这一个时辰的等待,对他们而言是那么的漫长,而心情又是那么的激动,那么的焦灼。
作为读者,我们也可据此推想,相聚后,两人又该是如何的情意缱绻,难舍难分,陶醉在甜蜜的喜悦中——明月皎皎,杨柳袅袅,灯影幢幢,情语喃喃,真是良辰、美景、赏心、乐事,四美俱至。而真正支撑美景的决定因素,是“人”,那个带来青春活力、带给“她”鲜活生命力的“他”,那个意中人。煦暖的节日气氛,与有情人的炽烈的情感,一明一暗,一动一静,相映成趣,既有天公作美,亦有人力玉成,可谓妙不可言。
可是,良宵苦短,华灯熄灭之际,也是梦醒时分,“他”和“她”不可避免地要回归惯常的生活,回归于礼教束缚之下的环境,昨夜的美好也只能化作甜蜜又苦涩的回忆,这就有了下片爱情命运的陡转。
又是元宵佳节,景色依旧宜人,场面一样热闹,但物是人非,缺少了“他”。环境的热烈温暖,却反衬了“她”心中的凄凉孤苦。如今,她形单影只,睹物思人,黯然神伤,怅惘不已。独立柳下,无助地等待日落月出;遥望天际,痴情地期待旧梦重现。但奇迹没有发生,那个“他”没有如去年那样依约而来,她心头的幻景,不是薄薄轻雾浮起,白马王子翩然而至,而是怒涛卷霜雪,要冲破“她”脆弱的心灵之堤——“泪湿春衫袖”就是那场风暴浪涛的结果。虽然是意料之中的,女主人公还是泣涕涟涟,泪若泉涌。“人”的缺位,可能是因为“他”已负心,可能是因为“他”遭受了巨大的压力和强力的阻拦,可能是由于其他难以抗拒的原因。无情的现实是,她今天成了世界上最不幸的人,遭受了“天”预设的铁幕——如昼的灯市后面,那真相是无际的夜空,幻想借偶然的机遇点亮灯火来冲破黑幕,那点光明,最终是要被无底的黑暗吞噬的。在这种情况下,“有情人终成眷属”永远是徒劳的呓语。“不见去年人,泪湿春衫袖”,看似轻描淡写,实则蕴涵浓浓的苦情,预示了悲剧的结局。
朗月明灯映柳梢,凄情冷泪度元宵,那个时代有情人的命运,也许就是这样
元宵节,又是一个浪漫柔情的节日,对妇女和青年人尤其是这样。封建社会里,妇女是没有独立外出的权利的,但是,元宵节是可以出来游玩的。她们结伴而行或走墙边,或过桥,走郊外,目的是驱病除灾,也起到了放松身心、愉悦情志的作用。街市赏灯,也为青年男女提供了与情人相会的机会,他们会在火树银花前眉目传情,在朦胧月光下倾吐心曲,在佛寺道观里为爱许愿。怪不得有人称元宵节为中国的“情人节”。对于这一点,宋词有名篇佳句展现。
“词别是一家”,婉约派主导的宋代词坛,抒情为其“当行本色”,词人更擅长刻画深婉蕴籍、幽深细腻的情感世界,意境较诗更精美清幽,情感更坦率真挚,画面更秾丽光艳。许多词人写下过情意绸缪的“元夕”词。
欧阳修的《生查子·元夕》意味隽永:
去年元夜时,花市灯如昼。月上柳梢头,人约黄昏后。
今年元夜时,月与灯依旧。不见去年人,泪湿春衫袖!
李白以降,历花间、南唐词派,直至两宋,男性词人多采用代言体,表现闺愁怨情,其抒情之哀婉缠绵,以至有甚于女词人。欧阳修的《元夕》,模拟失意女子的口吻,以细腻的笔触探入其幽深微妙的心灵底处,挖掘出积郁已久的幽愁暗恨,言简意赅,耐人寻味。
这首词通篇运用白描,章法上有似民歌的重章叠唱,上下两片成今昔对比,所以,其境皆素淡清新,其意却甘苦迥异。
站在现实的立足点上,回思去年今日,是中国诗人怀旧的一种传统的做法。他们的记忆永远是选择性的:崔护就将对城南旧事的无限思绪,定格于“人面桃花相映红”的画面上,令人想见往日那深挚热烈的一幕幕;欧阳修则先取“花市灯如昼”作为背景,那火树银花,熙来攘往的元宵节图景,是俗世狂欢的场面,是旧日中国难得的良辰美景。按尼采的话来说,它是日神阿波罗与酒神迪奥尼索斯的会合,有幻境,也有醉境,有对习惯乃至礼教的超越,更为有情人创设了相会的最佳时机——别人欢乐,他们可以闹中取静,见机行事,以遂平日之愿——面孔看似古板冰冷的都市,也有其温情脉脉开通的一面。
读者期待有那惊世骇俗的相见场面出现,然而,欧阳修却把它化为一片“空白”,留给我们悬念,留给我们想象的空间,这叫做“避实就虚”吧?他只写了此前的两个时辰:“月上柳梢头”,那是日入的酉时,“他”和“她”,在都城的一东一西,共同仰望着东升的月亮,它缓缓爬上来,挂在了梢尖初嫩的杨柳之上。此刻,春风骀荡,春机乍现,他们心旌摇荡,两情相悦,心有灵犀,只言片语,即已暗寄款款深情,只待婵娟高挂,早遂夙愿。两个人坐立不安,搔首踟蹰,因为此前禁锢得越久,束缚得越苦,此时就更期盼自由之欢,相聚之乐;可是,必待黄昏戌时后,方可腾出空间和时间给两位有情人,那时,他们才可借众人的忘我的狂欢,掩蔽悦情的情偶相聚。但这一个时辰的等待,对他们而言是那么的漫长,而心情又是那么的激动,那么的焦灼。
作为读者,我们也可据此推想,相聚后,两人又该是如何的情意缱绻,难舍难分,陶醉在甜蜜的喜悦中——明月皎皎,杨柳袅袅,灯影幢幢,情语喃喃,真是良辰、美景、赏心、乐事,四美俱至。而真正支撑美景的决定因素,是“人”,那个带来青春活力、带给“她”鲜活生命力的“他”,那个意中人。煦暖的节日气氛,与有情人的炽烈的情感,一明一暗,一动一静,相映成趣,既有天公作美,亦有人力玉成,可谓妙不可言。
可是,良宵苦短,华灯熄灭之际,也是梦醒时分,“他”和“她”不可避免地要回归惯常的生活,回归于礼教束缚之下的环境,昨夜的美好也只能化作甜蜜又苦涩的回忆,这就有了下片爱情命运的陡转。
又是元宵佳节,景色依旧宜人,场面一样热闹,但物是人非,缺少了“他”。环境的热烈温暖,却反衬了“她”心中的凄凉孤苦。如今,她形单影只,睹物思人,黯然神伤,怅惘不已。独立柳下,无助地等待日落月出;遥望天际,痴情地期待旧梦重现。但奇迹没有发生,那个“他”没有如去年那样依约而来,她心头的幻景,不是薄薄轻雾浮起,白马王子翩然而至,而是怒涛卷霜雪,要冲破“她”脆弱的心灵之堤——“泪湿春衫袖”就是那场风暴浪涛的结果。虽然是意料之中的,女主人公还是泣涕涟涟,泪若泉涌。“人”的缺位,可能是因为“他”已负心,可能是因为“他”遭受了巨大的压力和强力的阻拦,可能是由于其他难以抗拒的原因。无情的现实是,她今天成了世界上最不幸的人,遭受了“天”预设的铁幕——如昼的灯市后面,那真相是无际的夜空,幻想借偶然的机遇点亮灯火来冲破黑幕,那点光明,最终是要被无底的黑暗吞噬的。在这种情况下,“有情人终成眷属”永远是徒劳的呓语。“不见去年人,泪湿春衫袖”,看似轻描淡写,实则蕴涵浓浓的苦情,预示了悲剧的结局。
朗月明灯映柳梢,凄情冷泪度元宵,那个时代有情人的命运,也许就是这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