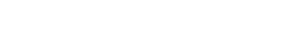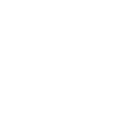烹饪经历了火烹、石烹、水烹、油烹四个发展阶段,火烹是最古老和原始的烹饪方法。传说中雷神的儿子伏羲氏带来火种之后,人们才渐渐远离了生食。火,令人类最终和动物界区分开来。因此烧烤的历史可以直追到人类对火的发现和管理使用。不过,如果在烧烤后面加上“文化”两个字来追究它的起源就相对复杂多了,见《史记•卷八十六•刺客传•专诸传》载:“酒既酣,公子光详为足疾,入窟室中,使专诸置匕首鱼炙之腹中而进之。”——鱼炙就是烤鱼,可见追溯到春秋时期是没有问题的,那会儿烤鱼就已经是“宫廷食品”了。
火烹主要的操作方法就是烧和烤。从直观感受来分辨,烧是令东西接触到火苗,因此时间较短(Grill);而烤是不接触火苗,只在火源附近利用火的热力来烘、熏、焙,因此时间较长(BBQ——Barbecue)。
烧烤可用的食材很广,畜禽海鲜、蔬菜水果无不可烤。从技法而言,如今演变出了白烤、红烤;腌烤、酥烤、挂糊烤、面烤;糊泥烤、串烤、叉烤、箅烤、挂炉烤;铁板烤、铁锅烤、竹筒烤;明炉烤、暗炉烤。
对于烧烤,我们要有组织有计划地吃……
原来我们的烹饪经历一直可以追溯到五六岁的时候。闭上眼睛,放自己回到儿时暮春的阳光中——作为一个农村长大的野孩子,进学堂念书之前是不是都有过烧胡豆豌豆、烧苞谷红苕、烤黄鳝泥鳅、烤麻雀画眉甚至耗子肉的经历?
每年春末,嫩胡豆和嫩豌豆刚出来的时候,小孩子最早尝鲜。在割完牛草回家的路上趁着暮色降临,偷偷在田边地头挤一荷包农业社的胡豆豌豆,把牛草送到社里牛圈交了,急急忙忙赶回家,借着煮饭或煮猪食的时候,折几根刷把签签把胡豆豌豆穿成一串,递到柴灶里去烧,不一会儿就外焦内嫩清香扑鼻了。心急火燎之下,根本顾不得烫不烫嘴,胡豆串横放在唇齿间一勒,焦脆的薄皮和鲜嫩香软的豆泥就留在了齿舌之间。没盐没油,它怎么就那么好吃呢?只是一不小心就会在嘴上留下黑灰,被大人发现后少不得换来一顿好骂。
要想大人不知道,那么就去山上烤。生产队有一匹山离村子很远,叫何二婆婆山,几乎每年的春末夏初,几个野孩子都会预谋去那里烧烤一次。待到快收麦子时,山顶的豌豆会早于山下黄熟,我们上午去小河边的沟渠里弄些鲫鱼泥鳅,砍几节新鲜竹筒,装上水,把洗净的鲫鱼和泥鳅装进去,再挤点嫩胡豆豌豆进去,放些盐,最后勒一把新鲜胡豆叶子把竹筒塞紧。
吃过午饭,几个人就偷偷摸摸地往何二婆婆山赶。四月的阳光,会把土路晒得温热温热的。路两旁的眼镜草和铁匠草往小路中间长着,光脚走在上面,绵绵软软地很是舒服,地里的麦子在阳光下散发着干燥的麦香。
何二婆婆山顶,多是裸露在外的光洁石面,仅少数地方有一层浅土,生产队只在上面种了些豌豆和麦子,麦子长得稀稀拉拉。我们先用双脚把已经被晒干的豌豆藤踢成一堆,再拖到那块略凹的光洁石面上,把用石块把竹筒夹紧放在里面,点燃豌豆藤,等火势蔓延开来,便呼啦啦跑去半山腰的“蛮子洞”去藏起来。
估计火熄了,又呼啦啦一齐跑回山顶,顾不了烫手的灰烬,又吹又刨地捡石面上的豌豆,黄的黑的,焦的煳的,只管一边往嘴里塞一边往荷包里装,荷包贴着腰还是滚烫滚烫的呢。最后才把竹筒刨出来,抠开竹筒口子的胡豆叶,先一人一口地喝那香浓的鱼汤,最后再吃那里面的鱼和泥鳅,咸香鲜腥,那些胡豆豌豆也煮开了花。
等端阳一过,最早成熟的嫩苞谷多数是被烧来吃掉的。
嫩苞谷一般是在煮饭的时候放到柴灶的灰堆里埋着烧,其间还要用火钳夹着翻一次以使受热均匀。苞谷烧得好的,掏出来只苞谷籽儿最顶上有一点焦黑,其余部分都是金黄色的。顺势在灶台石壁上拍去柴灰,趁着烫抹籽吃,又糯又香,吃两个就不大吃得下饭了。那味道,远比现在城里卖的烤玉米好。
到快割谷子的时节,又该烤青蛙了!绿皮青蛙我们叫它青鬼,黄皮青蛙叫蛇鬼。每年水稻长封林的时候,这东西便多了起来,到处呱呱乱叫,逗得野孩子们心痒——钓青蛙!钓青蛙不需要多少技术,随便弄根不长的细竹竿,细麻绳或是尼龙丝做钓线,钓饵只要一个,是用蚯蚓穿成的一个圈儿,然后沿着稻田田埂走,听哪有叫声就把钓饵垂过去,让它在谷子林里一跳一跳地,便会有青蛙跳来咬着钓饵不肯松口,提起短钓竿往左手布口袋一抖,它才落下。
如果钓得少,拿回家撕皮去肚之后只抹一层盐,用青菜叶子(有时也用荷叶或芭蕉芋叶子)包起来,扯两根谷草横竖一捆,埋在灶膛柴灰里面烤,一顿饭时间就好。那个香啊!烧得焦脆的菜叶子还没剥开,香气就扑了出来,直惹得人馋涎不止。剥到内层,便有滚烫的汁液从菜叶间流出来,忍不住了可以先舔食之,甚至先把菜叶吃掉一半再吃蛙肉,那蛙肉已烤成了淡黄色,鲜嫩无比奇香扑鼻,嚼起来还有些弹牙,细小的骨头也酥脆了……人间至味啊!如果钓得多了还可以用来炒,加泡椒、泡姜,如果可能再加一勺醪糟,这些滋味真让人不敢在深夜里想起!(幼时还不知道青蛙会成为保护动物,所以那美味只有深深地留在记忆中了。)
入冬以后,烤得最多便是红苕了,随时随地都可以埋两个在柴灶里面。烤红苕火不能大,时间不短,中间还要翻动一两次。这样烤出来只有两头是焦黑的,红苕皮呈暗红色,已经烤成一层壳,焦黄而香脆。掰开来里面却是淡黄色的,冒着袅袅白汽,诱人的香味也随之飘了出来。吃要趁烫啊!咧嘴呲牙嘘着气,就是要吃这份热烫的天然香味!
冬天还有一样东西可以烤——麻雀。也许是因为这东西不太好弄,所以显得格外的香。麻雀多是用面筛来捕的(好象有一篇课文中讲过),冬天可供麻雀啄食的东西越来越少,尤其下雪天更少,所以弄些碎苞谷或米粒儿撒在地上作诱饵,上面用小竹棍儿支个面筛,远远地系根长绳在竹棍儿上,见有麻雀跳进去便把竹棍儿拉倒。不过川南很少下雪,而麻雀这鬼东西太机灵了,所以辛苦半天也不见得能捕到两只。捕到之后生褪了毛,抹了盐,摘一张芭蕉芋叶子紧紧裹上几层,放灶膛里烤。烤熟之后需要细细地撕来吃,麻雀肉较之蛙肉要老,不过肉香味更为浓郁,常会被撞见的大人要求分食一腿呢。
这些久远的视听味触觉记忆,几乎年龄稍长的人都有过,特别是在农村长大的。它常令我在心境特别宁静的时候想起,甚至是在梦里重演。那些除了盐几乎不用任何调味料烧烤出来的味道时常使我失魂落魄,潜意识当中难说没有对先祖使用时间最长的烹食方法的认同和重复。成年后,我几乎再也品尝不到儿时的美味,不知是再没有儿时极尽简单的吃食环境和食欲需求,还是不再有儿时那么丰富的味蕾。
记忆中的东西终将越来越远……
火烹主要的操作方法就是烧和烤。从直观感受来分辨,烧是令东西接触到火苗,因此时间较短(Grill);而烤是不接触火苗,只在火源附近利用火的热力来烘、熏、焙,因此时间较长(BBQ——Barbecue)。
烧烤可用的食材很广,畜禽海鲜、蔬菜水果无不可烤。从技法而言,如今演变出了白烤、红烤;腌烤、酥烤、挂糊烤、面烤;糊泥烤、串烤、叉烤、箅烤、挂炉烤;铁板烤、铁锅烤、竹筒烤;明炉烤、暗炉烤。
对于烧烤,我们要有组织有计划地吃……
原来我们的烹饪经历一直可以追溯到五六岁的时候。闭上眼睛,放自己回到儿时暮春的阳光中——作为一个农村长大的野孩子,进学堂念书之前是不是都有过烧胡豆豌豆、烧苞谷红苕、烤黄鳝泥鳅、烤麻雀画眉甚至耗子肉的经历?
每年春末,嫩胡豆和嫩豌豆刚出来的时候,小孩子最早尝鲜。在割完牛草回家的路上趁着暮色降临,偷偷在田边地头挤一荷包农业社的胡豆豌豆,把牛草送到社里牛圈交了,急急忙忙赶回家,借着煮饭或煮猪食的时候,折几根刷把签签把胡豆豌豆穿成一串,递到柴灶里去烧,不一会儿就外焦内嫩清香扑鼻了。心急火燎之下,根本顾不得烫不烫嘴,胡豆串横放在唇齿间一勒,焦脆的薄皮和鲜嫩香软的豆泥就留在了齿舌之间。没盐没油,它怎么就那么好吃呢?只是一不小心就会在嘴上留下黑灰,被大人发现后少不得换来一顿好骂。
要想大人不知道,那么就去山上烤。生产队有一匹山离村子很远,叫何二婆婆山,几乎每年的春末夏初,几个野孩子都会预谋去那里烧烤一次。待到快收麦子时,山顶的豌豆会早于山下黄熟,我们上午去小河边的沟渠里弄些鲫鱼泥鳅,砍几节新鲜竹筒,装上水,把洗净的鲫鱼和泥鳅装进去,再挤点嫩胡豆豌豆进去,放些盐,最后勒一把新鲜胡豆叶子把竹筒塞紧。
吃过午饭,几个人就偷偷摸摸地往何二婆婆山赶。四月的阳光,会把土路晒得温热温热的。路两旁的眼镜草和铁匠草往小路中间长着,光脚走在上面,绵绵软软地很是舒服,地里的麦子在阳光下散发着干燥的麦香。
何二婆婆山顶,多是裸露在外的光洁石面,仅少数地方有一层浅土,生产队只在上面种了些豌豆和麦子,麦子长得稀稀拉拉。我们先用双脚把已经被晒干的豌豆藤踢成一堆,再拖到那块略凹的光洁石面上,把用石块把竹筒夹紧放在里面,点燃豌豆藤,等火势蔓延开来,便呼啦啦跑去半山腰的“蛮子洞”去藏起来。
估计火熄了,又呼啦啦一齐跑回山顶,顾不了烫手的灰烬,又吹又刨地捡石面上的豌豆,黄的黑的,焦的煳的,只管一边往嘴里塞一边往荷包里装,荷包贴着腰还是滚烫滚烫的呢。最后才把竹筒刨出来,抠开竹筒口子的胡豆叶,先一人一口地喝那香浓的鱼汤,最后再吃那里面的鱼和泥鳅,咸香鲜腥,那些胡豆豌豆也煮开了花。
等端阳一过,最早成熟的嫩苞谷多数是被烧来吃掉的。
嫩苞谷一般是在煮饭的时候放到柴灶的灰堆里埋着烧,其间还要用火钳夹着翻一次以使受热均匀。苞谷烧得好的,掏出来只苞谷籽儿最顶上有一点焦黑,其余部分都是金黄色的。顺势在灶台石壁上拍去柴灰,趁着烫抹籽吃,又糯又香,吃两个就不大吃得下饭了。那味道,远比现在城里卖的烤玉米好。
到快割谷子的时节,又该烤青蛙了!绿皮青蛙我们叫它青鬼,黄皮青蛙叫蛇鬼。每年水稻长封林的时候,这东西便多了起来,到处呱呱乱叫,逗得野孩子们心痒——钓青蛙!钓青蛙不需要多少技术,随便弄根不长的细竹竿,细麻绳或是尼龙丝做钓线,钓饵只要一个,是用蚯蚓穿成的一个圈儿,然后沿着稻田田埂走,听哪有叫声就把钓饵垂过去,让它在谷子林里一跳一跳地,便会有青蛙跳来咬着钓饵不肯松口,提起短钓竿往左手布口袋一抖,它才落下。
如果钓得少,拿回家撕皮去肚之后只抹一层盐,用青菜叶子(有时也用荷叶或芭蕉芋叶子)包起来,扯两根谷草横竖一捆,埋在灶膛柴灰里面烤,一顿饭时间就好。那个香啊!烧得焦脆的菜叶子还没剥开,香气就扑了出来,直惹得人馋涎不止。剥到内层,便有滚烫的汁液从菜叶间流出来,忍不住了可以先舔食之,甚至先把菜叶吃掉一半再吃蛙肉,那蛙肉已烤成了淡黄色,鲜嫩无比奇香扑鼻,嚼起来还有些弹牙,细小的骨头也酥脆了……人间至味啊!如果钓得多了还可以用来炒,加泡椒、泡姜,如果可能再加一勺醪糟,这些滋味真让人不敢在深夜里想起!(幼时还不知道青蛙会成为保护动物,所以那美味只有深深地留在记忆中了。)
入冬以后,烤得最多便是红苕了,随时随地都可以埋两个在柴灶里面。烤红苕火不能大,时间不短,中间还要翻动一两次。这样烤出来只有两头是焦黑的,红苕皮呈暗红色,已经烤成一层壳,焦黄而香脆。掰开来里面却是淡黄色的,冒着袅袅白汽,诱人的香味也随之飘了出来。吃要趁烫啊!咧嘴呲牙嘘着气,就是要吃这份热烫的天然香味!
冬天还有一样东西可以烤——麻雀。也许是因为这东西不太好弄,所以显得格外的香。麻雀多是用面筛来捕的(好象有一篇课文中讲过),冬天可供麻雀啄食的东西越来越少,尤其下雪天更少,所以弄些碎苞谷或米粒儿撒在地上作诱饵,上面用小竹棍儿支个面筛,远远地系根长绳在竹棍儿上,见有麻雀跳进去便把竹棍儿拉倒。不过川南很少下雪,而麻雀这鬼东西太机灵了,所以辛苦半天也不见得能捕到两只。捕到之后生褪了毛,抹了盐,摘一张芭蕉芋叶子紧紧裹上几层,放灶膛里烤。烤熟之后需要细细地撕来吃,麻雀肉较之蛙肉要老,不过肉香味更为浓郁,常会被撞见的大人要求分食一腿呢。
这些久远的视听味触觉记忆,几乎年龄稍长的人都有过,特别是在农村长大的。它常令我在心境特别宁静的时候想起,甚至是在梦里重演。那些除了盐几乎不用任何调味料烧烤出来的味道时常使我失魂落魄,潜意识当中难说没有对先祖使用时间最长的烹食方法的认同和重复。成年后,我几乎再也品尝不到儿时的美味,不知是再没有儿时极尽简单的吃食环境和食欲需求,还是不再有儿时那么丰富的味蕾。
记忆中的东西终将越来越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