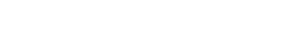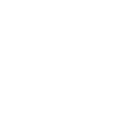三十六
第二天,是这里的冬天难得一见的好天气。万里无云,天空一片碧蓝,没有平日那么的潮湿,干干爽爽。太阳光洒遍了大地,给快要冻僵的世间万物带来了一份惬意的温暖,照在人身上暖洋洋的,让人昏昏欲睡,很是舒服。
九镇上的阿姨大妈们都趁着这个好天气,赶紧洗完了该洗的衣服,翻箱倒柜的把家里所有的被褥,衣物都一起拿了出来,晾在阳光充足的院子里,街道上。干完了活儿之后,大家或是三五人坐上一桌,打打麻将、扑克;或是搬个凳子,泡上杯热茶,拿着给小辈、老公们织的毛衣,三大姑五大婆地开始闲扯起来。
这是一个安详美好的艳阳天,一片升平景象。
记得有位我很喜欢的武侠作家,在他的作品中有过一段话:“这是个杀人的好天气,杀了人,血流在地上也干得快,我喜欢在这种天气杀人。”
同样,这也是个打架的好天气,打完架之后流的血也一定会干得更快。
在大多数人都惬意而慵懒地享受着这个舒适的艳阳天时,我们兄弟却都进入了高度的兴奋和紧张中,为晚上即将到来的一战,做着各种各样的准备。
中午吃完饭,我们所有人都以不同的理由向老师请了假或者直接逃了课,在校门口集合。
然后我们找三哥去拿了他帮我们准备的一些东西,一起穿过了十字路口和新码头、上下街,来到了九镇大桥的下面。
九镇有一条很漂亮的母亲河,河水清澈明亮,水流平缓安静。渔夫们撑着竹篙,架着渔船,船头蹲着一排排的水老鸭(鸬鹚),一声召唤,水老鸭就纷纷跳入了水中。片刻功夫,又都从水底冒出了头,渔夫一手抓住水老鸭鼓胀的脖子,另一只手从下往上顺着水老鸭的脖子那么轻轻一撸,一条活蹦乱跳,银光闪闪的鱼就从水老鸭的嘴里跳将出来。
大桥靠九镇这边的下面有一块比较大的场地,数十米见方,一到晚间,除了疯子,绝不会有人来。
我们和大脑壳约着摆场的地方就在这里。
场子的边上是一排沿着河岸蜿蜒而建的住房,有些房子被房东老板改成了私人小旅馆,其中的几家靠我们晚上要干架的这片空地非常近。我们仔细察看了下这几家小旅馆和场地的距离,小旅馆的窗口和阳台离地面高的也就是两米五左右,低的大概一米七八,一个年轻人可以很容易地爬上爬下。非常好!
看完了旅馆这边,我们又仔细察看了桥下的这片空地。空地靠桥的那边比对桥这一边的地势要低一些,而且在中间的地方有一个低矮的小土坎,跑起来一下子就可以跳过去。这更好了!
看好了地形,我们开始准备。拿起三哥给我们事先预备好的七八把锄头、铁锹和一些很薄的三合板,就在那个小土坎的一侧开始挖了起来,挖出来的土直接倒在河里面,不是很环保但是方便。一边挖一边玩笑打闹,中间,还有几位住在边上的住户问我们在这里搞什么,我们就说明天搞烧烤,今天做准备。
大概三个多小时,四个小时不到,一条七八十公分深,四五十公分宽,十多米长的沟就挖好了。
在沟上盖好三合板,板子上铺上一层细细的浮土,地儿还搞了些乱草叶细树棍之类的洒在了上面。连记号都不用做,记住那个小土坎就是。土坑挖好,我们就在河里洗了手,又到刚才看好的几间靠近场地的旅馆里,订下了三间最合适的房。
一切准备就绪。只欠东风。
很多次,我问过自己:“胡钦,你到底是不是个胆子很大的人?”
结论是——不是。
多我的兄弟们那儿了解,他们也问过自己同样的问题,他们的结论也是一样。
我们跟普通人一样都有很多的顾忌,比如人性道德、家庭亲人、朋友感情、正常生活等等,所以在某些时刻来临时,会有一丝胆怯。但是险儿是个例外,他除了将我们有数几个人和他的家人放在心上之外,好像连自己都不是太在乎。这样的人做兄弟是不错的,但是做敌人就太可怕了,就算他不是将首,也一定是万军丛中取敌将之首的先锋猛将。
在这个晚上,他又一次印证了我们的观点。
我还记得,那天我们回去后,三哥在巨龙开了个包厢,请我们所有人一起吃饭。
到的时候,三哥和明哥,还有牯牛、癫子(这两位都是三哥手下非常得力的干将,介于兄弟和小弟之间)等人都已经等在包厢,正坐在桌子周围聊着什么,饭菜也早已经摆上了桌子。
“事情都搞好了吗?”三哥一看见我们就说。
“啊,搞好了,就看今天晚上了。”袁伟答道。
“先坐下,边吃饭边说。”明哥答道。
坐下后,三哥亲自给我们每个人倒了一满杯啤酒,“今天,你们就少喝点,就喝这一杯啤酒,晚上还要办事的。等你们搞赢了,还到这里来,我今天就在这里等。你们来了,我们就喝酒,你们不来,我今天就直接去红杰家里,办他全家!”三哥一把从怀里掏出了一支手枪,啪的一声拍在桌子上。
全场人都惊呆了!
那一瞬间,我真的很想哭,三哥这个举动在一瞬间使气氛悲壮起来。
我忽然有种燕太子丹易水河畔送荆轲的感受,“风萧萧兮易水寒,壮士一去兮不复还。”似乎此去不是为了私人恩怨去和大脑壳打架,而是在国难当头的时刻,为了民族国家大义去慷慨赴死。成为“引刀成一快,不负少年头”的豪情义士。
我当时的感觉无法言表,一些紧张,一些感动,一些慷慨,一些冲动,百感交集,鼻子一阵酸楚。这份兄弟情义!这份让我感到死了都有靠山的安全感!三哥不愧是大哥!
包厢里一片安静,我转头一看,地儿和袁伟脸上都有泪痕闪动了。
三哥的一席话,把我们下午挖坑时候的欢乐气氛冲得荡然无存。我们还从来没有经历过江湖上真正的斗殴,下意识地觉得这次和以前的打架没有什么区别,尤其是在我们想出了很多办法之后,我们觉得胜利完全在望,大脑壳他们将会像是十三太保一样,直接被我们办倒。不会有人受伤,不会有人哭泣,更不会有人死亡。
但是三哥的一席话,却突然让我们明白了,今天晚上将要发生的事和以往是不一样的。只要我们敢去,他们敢来,那么今天就是一场残酷凶险的混战。
一旦参加,刀枪无眼,生死之间,各安天命。
这一刻,我们突然明白过来,这不再是我们作为学生身份的打架,而是作为古惑仔的真正火拼。
计划虽定,但成事在天,谁输谁赢,无人得知。
突如其来的紧张情绪蔓延开来,包括了今晚将要参战的每一个人,包厢内一片寂静,只有险儿还在不停玩着他的打火机,单调又空洞的“嚓嚓”声,让每个人的感觉更为压抑。
“哭什么哭,打个架,有什么关系唦。义色,你也是,把个小孩子们吓成这样。来来来,喝酒,明天太阳升起的时候,你们就是大哥了!我先干为敬!”明哥端起自己面前的杯子,一口喝掉。
明哥的话又马上激起了我们几个的万丈豪情,方才低落的情绪重新高涨起来。
“三哥明哥,干,我们兄弟不会丢你的脸。今天我们就搞死大脑壳,兄弟们,一起来。”武昇首先站起,一口喝掉的杯子里面的酒,然后做了个让我们事后笑了很久的动作。砰的一声,他居然学着电视里的样子,把杯子猛地一下摔在了地上。
“给你们说件事,你们先不要害怕。”三哥喝完接着说道。
“说吧,三哥,没有什么的,怕我们今天就不会决心搞了。”
“有朋友给我说,红杰自己没有出面,不过他确实从市里帮大脑壳叫了人过来,可能带了把鸟铳。但是你们不要怕,铁明会和你们一起去,拿枪的人你们就交给他。这种事我们见得多了,真正敢开枪的没有几个。红杰要真敢搞,他自己就上了,何必叫人。他们肯定不会首先开枪的,这点我敢保证。红杰无非就是怕他的小弟出大事,拿把枪吓吓你们,也给那些学生壮下胆。我先给你们说声,你们不要做得太过,逼着人家把事搞大了。听到没?”
“知道了,三哥。没事的,有枪就有枪吧,你说不敢搞,我相信你。”我相信三哥,就算不信,我也只能这么说了,事到临头,不能先败了自己的士气。
奇怪的是,险儿听了这话后,一反常态地瞟了瞟三哥,却没有吭声,当时我以为他也是有些顾忌和害怕。
三个小时后,我知道我错了,错得很离谱。
“那好,我们先吃吧。”
在一片兴奋而奇特的气氛中,我们吃完了饭。
“牯牛,你从后面把东西拿过来。”三哥说道。牯牛应了一声出去了,片刻后,拎着两个大袋子走了进来。
“你们自己选吧。”三哥对着袋子一指,牯牛同时把袋子放在地上,打了开来,一整袋都是刀具,我们都围上前挑选。
就直接武昇拿了一把管杀在手上。什么是管杀?这是非常牛逼的东西,是我们那边的特产,可以说是除了枪最霸道的武器。
选一块好钢板,在工厂找人用砂轮抛光打磨成一把大一号的马刀形状,然后再找根铁管,把刀后面车上螺旋纹,铁管上也车上相应的螺旋纹。单拿在手上就是一把刀,接上铁管就是一把大刀,非常威猛!
武昇拿起管杀后,高大魁梧的身材和霸道的管杀浑然一体,给我们的感觉,好像他天生就是为拿管杀的,非常匹配。
除了管杀,还有几把杀猪刀和砍刀。在我们这边,杀猪的屠夫用的刀是有很多种型号的,最大的就是杀猪切肉用的屠刀,稍小的是砍骨头的,再小一号的是用来捅猪脖子放血的(我和小二爷、地儿选的就是这种),还小一号的好像是剔骨头的,除了杀人,没见过有人用。
我们几兄弟都选了不同型号的杀猪刀,砍刀就分给了简杰他们几个。险儿拿起了另外一把管杀,武昇是马刀形状的,比较好看,他选的就是一把像板刀一样长方形的管杀,不是很漂亮,但是一看就知道,砍上去不得了。
我想了下,还是走过去,要险儿用管杀和小敏手上的砍刀调换,他死都不愿意,最后没有办法,让袁伟用砍骨头的杀猪刀和他换了。
三哥看我们选完了武器,再从旁边拿出了三个书包,把另一个袋子打开了。“你们把这里面的东西放在书包里,用的时候再拿。”
第二天,是这里的冬天难得一见的好天气。万里无云,天空一片碧蓝,没有平日那么的潮湿,干干爽爽。太阳光洒遍了大地,给快要冻僵的世间万物带来了一份惬意的温暖,照在人身上暖洋洋的,让人昏昏欲睡,很是舒服。
九镇上的阿姨大妈们都趁着这个好天气,赶紧洗完了该洗的衣服,翻箱倒柜的把家里所有的被褥,衣物都一起拿了出来,晾在阳光充足的院子里,街道上。干完了活儿之后,大家或是三五人坐上一桌,打打麻将、扑克;或是搬个凳子,泡上杯热茶,拿着给小辈、老公们织的毛衣,三大姑五大婆地开始闲扯起来。
这是一个安详美好的艳阳天,一片升平景象。
记得有位我很喜欢的武侠作家,在他的作品中有过一段话:“这是个杀人的好天气,杀了人,血流在地上也干得快,我喜欢在这种天气杀人。”
同样,这也是个打架的好天气,打完架之后流的血也一定会干得更快。
在大多数人都惬意而慵懒地享受着这个舒适的艳阳天时,我们兄弟却都进入了高度的兴奋和紧张中,为晚上即将到来的一战,做着各种各样的准备。
中午吃完饭,我们所有人都以不同的理由向老师请了假或者直接逃了课,在校门口集合。
然后我们找三哥去拿了他帮我们准备的一些东西,一起穿过了十字路口和新码头、上下街,来到了九镇大桥的下面。
九镇有一条很漂亮的母亲河,河水清澈明亮,水流平缓安静。渔夫们撑着竹篙,架着渔船,船头蹲着一排排的水老鸭(鸬鹚),一声召唤,水老鸭就纷纷跳入了水中。片刻功夫,又都从水底冒出了头,渔夫一手抓住水老鸭鼓胀的脖子,另一只手从下往上顺着水老鸭的脖子那么轻轻一撸,一条活蹦乱跳,银光闪闪的鱼就从水老鸭的嘴里跳将出来。
大桥靠九镇这边的下面有一块比较大的场地,数十米见方,一到晚间,除了疯子,绝不会有人来。
我们和大脑壳约着摆场的地方就在这里。
场子的边上是一排沿着河岸蜿蜒而建的住房,有些房子被房东老板改成了私人小旅馆,其中的几家靠我们晚上要干架的这片空地非常近。我们仔细察看了下这几家小旅馆和场地的距离,小旅馆的窗口和阳台离地面高的也就是两米五左右,低的大概一米七八,一个年轻人可以很容易地爬上爬下。非常好!
看完了旅馆这边,我们又仔细察看了桥下的这片空地。空地靠桥的那边比对桥这一边的地势要低一些,而且在中间的地方有一个低矮的小土坎,跑起来一下子就可以跳过去。这更好了!
看好了地形,我们开始准备。拿起三哥给我们事先预备好的七八把锄头、铁锹和一些很薄的三合板,就在那个小土坎的一侧开始挖了起来,挖出来的土直接倒在河里面,不是很环保但是方便。一边挖一边玩笑打闹,中间,还有几位住在边上的住户问我们在这里搞什么,我们就说明天搞烧烤,今天做准备。
大概三个多小时,四个小时不到,一条七八十公分深,四五十公分宽,十多米长的沟就挖好了。
在沟上盖好三合板,板子上铺上一层细细的浮土,地儿还搞了些乱草叶细树棍之类的洒在了上面。连记号都不用做,记住那个小土坎就是。土坑挖好,我们就在河里洗了手,又到刚才看好的几间靠近场地的旅馆里,订下了三间最合适的房。
一切准备就绪。只欠东风。
很多次,我问过自己:“胡钦,你到底是不是个胆子很大的人?”
结论是——不是。
多我的兄弟们那儿了解,他们也问过自己同样的问题,他们的结论也是一样。
我们跟普通人一样都有很多的顾忌,比如人性道德、家庭亲人、朋友感情、正常生活等等,所以在某些时刻来临时,会有一丝胆怯。但是险儿是个例外,他除了将我们有数几个人和他的家人放在心上之外,好像连自己都不是太在乎。这样的人做兄弟是不错的,但是做敌人就太可怕了,就算他不是将首,也一定是万军丛中取敌将之首的先锋猛将。
在这个晚上,他又一次印证了我们的观点。
我还记得,那天我们回去后,三哥在巨龙开了个包厢,请我们所有人一起吃饭。
到的时候,三哥和明哥,还有牯牛、癫子(这两位都是三哥手下非常得力的干将,介于兄弟和小弟之间)等人都已经等在包厢,正坐在桌子周围聊着什么,饭菜也早已经摆上了桌子。
“事情都搞好了吗?”三哥一看见我们就说。
“啊,搞好了,就看今天晚上了。”袁伟答道。
“先坐下,边吃饭边说。”明哥答道。
坐下后,三哥亲自给我们每个人倒了一满杯啤酒,“今天,你们就少喝点,就喝这一杯啤酒,晚上还要办事的。等你们搞赢了,还到这里来,我今天就在这里等。你们来了,我们就喝酒,你们不来,我今天就直接去红杰家里,办他全家!”三哥一把从怀里掏出了一支手枪,啪的一声拍在桌子上。
全场人都惊呆了!
那一瞬间,我真的很想哭,三哥这个举动在一瞬间使气氛悲壮起来。
我忽然有种燕太子丹易水河畔送荆轲的感受,“风萧萧兮易水寒,壮士一去兮不复还。”似乎此去不是为了私人恩怨去和大脑壳打架,而是在国难当头的时刻,为了民族国家大义去慷慨赴死。成为“引刀成一快,不负少年头”的豪情义士。
我当时的感觉无法言表,一些紧张,一些感动,一些慷慨,一些冲动,百感交集,鼻子一阵酸楚。这份兄弟情义!这份让我感到死了都有靠山的安全感!三哥不愧是大哥!
包厢里一片安静,我转头一看,地儿和袁伟脸上都有泪痕闪动了。
三哥的一席话,把我们下午挖坑时候的欢乐气氛冲得荡然无存。我们还从来没有经历过江湖上真正的斗殴,下意识地觉得这次和以前的打架没有什么区别,尤其是在我们想出了很多办法之后,我们觉得胜利完全在望,大脑壳他们将会像是十三太保一样,直接被我们办倒。不会有人受伤,不会有人哭泣,更不会有人死亡。
但是三哥的一席话,却突然让我们明白了,今天晚上将要发生的事和以往是不一样的。只要我们敢去,他们敢来,那么今天就是一场残酷凶险的混战。
一旦参加,刀枪无眼,生死之间,各安天命。
这一刻,我们突然明白过来,这不再是我们作为学生身份的打架,而是作为古惑仔的真正火拼。
计划虽定,但成事在天,谁输谁赢,无人得知。
突如其来的紧张情绪蔓延开来,包括了今晚将要参战的每一个人,包厢内一片寂静,只有险儿还在不停玩着他的打火机,单调又空洞的“嚓嚓”声,让每个人的感觉更为压抑。
“哭什么哭,打个架,有什么关系唦。义色,你也是,把个小孩子们吓成这样。来来来,喝酒,明天太阳升起的时候,你们就是大哥了!我先干为敬!”明哥端起自己面前的杯子,一口喝掉。
明哥的话又马上激起了我们几个的万丈豪情,方才低落的情绪重新高涨起来。
“三哥明哥,干,我们兄弟不会丢你的脸。今天我们就搞死大脑壳,兄弟们,一起来。”武昇首先站起,一口喝掉的杯子里面的酒,然后做了个让我们事后笑了很久的动作。砰的一声,他居然学着电视里的样子,把杯子猛地一下摔在了地上。
“给你们说件事,你们先不要害怕。”三哥喝完接着说道。
“说吧,三哥,没有什么的,怕我们今天就不会决心搞了。”
“有朋友给我说,红杰自己没有出面,不过他确实从市里帮大脑壳叫了人过来,可能带了把鸟铳。但是你们不要怕,铁明会和你们一起去,拿枪的人你们就交给他。这种事我们见得多了,真正敢开枪的没有几个。红杰要真敢搞,他自己就上了,何必叫人。他们肯定不会首先开枪的,这点我敢保证。红杰无非就是怕他的小弟出大事,拿把枪吓吓你们,也给那些学生壮下胆。我先给你们说声,你们不要做得太过,逼着人家把事搞大了。听到没?”
“知道了,三哥。没事的,有枪就有枪吧,你说不敢搞,我相信你。”我相信三哥,就算不信,我也只能这么说了,事到临头,不能先败了自己的士气。
奇怪的是,险儿听了这话后,一反常态地瞟了瞟三哥,却没有吭声,当时我以为他也是有些顾忌和害怕。
三个小时后,我知道我错了,错得很离谱。
“那好,我们先吃吧。”
在一片兴奋而奇特的气氛中,我们吃完了饭。
“牯牛,你从后面把东西拿过来。”三哥说道。牯牛应了一声出去了,片刻后,拎着两个大袋子走了进来。
“你们自己选吧。”三哥对着袋子一指,牯牛同时把袋子放在地上,打了开来,一整袋都是刀具,我们都围上前挑选。
就直接武昇拿了一把管杀在手上。什么是管杀?这是非常牛逼的东西,是我们那边的特产,可以说是除了枪最霸道的武器。
选一块好钢板,在工厂找人用砂轮抛光打磨成一把大一号的马刀形状,然后再找根铁管,把刀后面车上螺旋纹,铁管上也车上相应的螺旋纹。单拿在手上就是一把刀,接上铁管就是一把大刀,非常威猛!
武昇拿起管杀后,高大魁梧的身材和霸道的管杀浑然一体,给我们的感觉,好像他天生就是为拿管杀的,非常匹配。
除了管杀,还有几把杀猪刀和砍刀。在我们这边,杀猪的屠夫用的刀是有很多种型号的,最大的就是杀猪切肉用的屠刀,稍小的是砍骨头的,再小一号的是用来捅猪脖子放血的(我和小二爷、地儿选的就是这种),还小一号的好像是剔骨头的,除了杀人,没见过有人用。
我们几兄弟都选了不同型号的杀猪刀,砍刀就分给了简杰他们几个。险儿拿起了另外一把管杀,武昇是马刀形状的,比较好看,他选的就是一把像板刀一样长方形的管杀,不是很漂亮,但是一看就知道,砍上去不得了。
我想了下,还是走过去,要险儿用管杀和小敏手上的砍刀调换,他死都不愿意,最后没有办法,让袁伟用砍骨头的杀猪刀和他换了。
三哥看我们选完了武器,再从旁边拿出了三个书包,把另一个袋子打开了。“你们把这里面的东西放在书包里,用的时候再拿。”